伟大的转型美国市场一体化和金融的力量.pdf
http://www.100md.com
2019年12月26日
 |
| 第1页 |
 |
| 第9页 |
 |
| 第19页 |
 |
| 第23页 |
 |
| 第37页 |
 |
| 第199页 |
参见附件(4128KB,262页)。
伟大的转型美国市场一体化和金融的力量是由诺姆·马格尔所著,作者从多个角度出发,讲述了为什么美国能从农产品出口国,转型成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

伟大的转型美国市场一体化和金融的力量预览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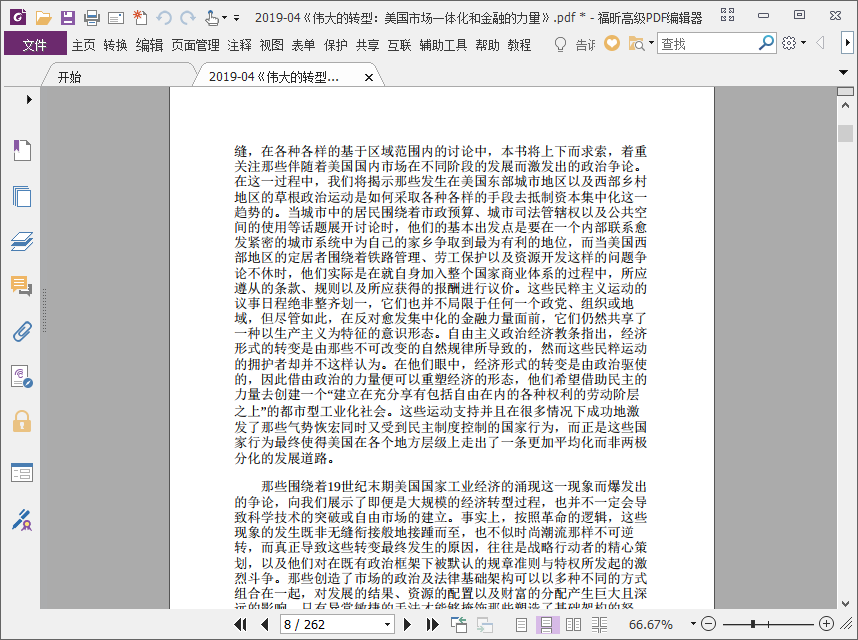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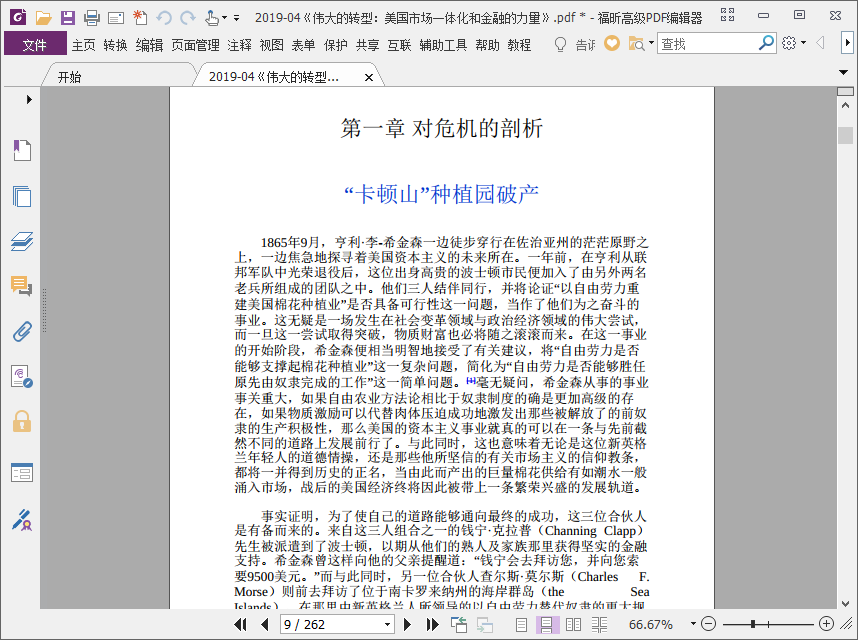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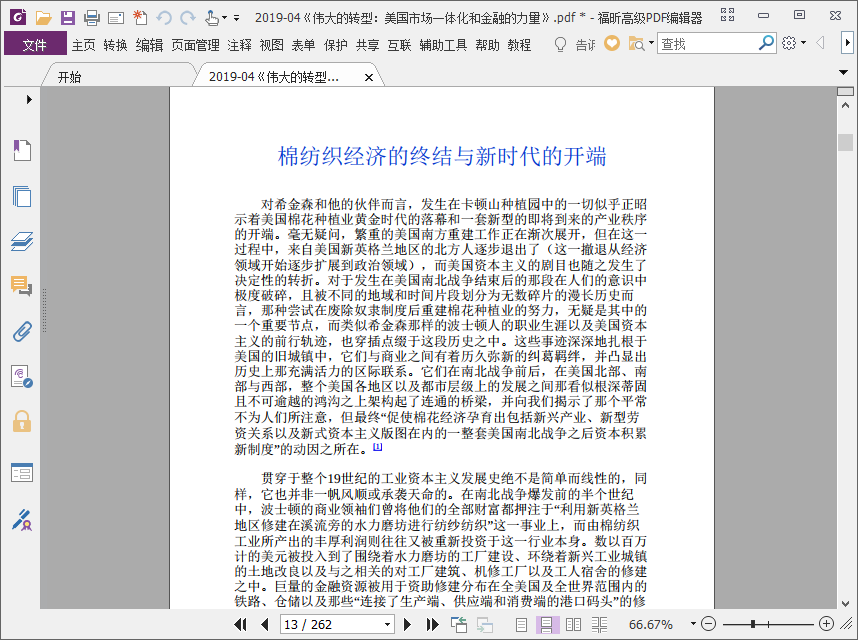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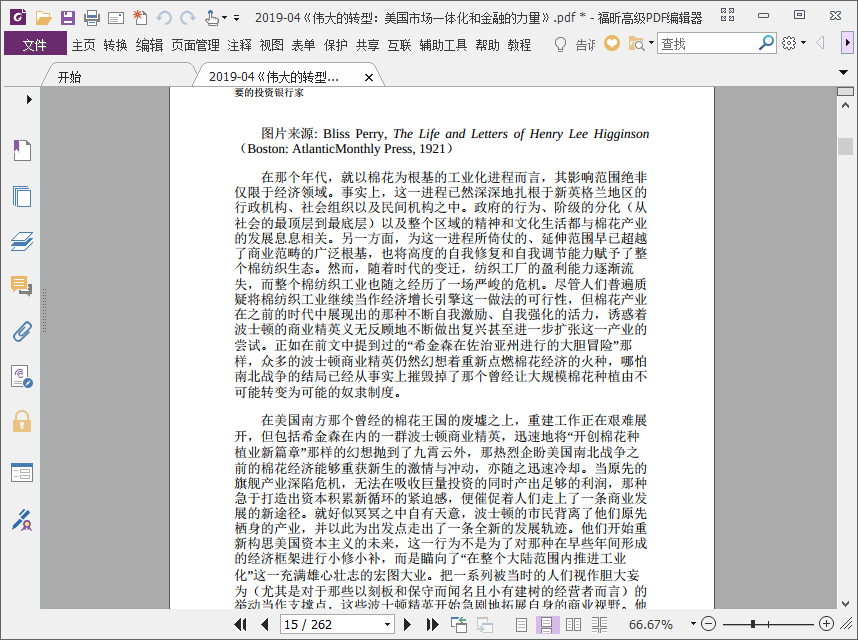
《伟大的转型》目录
第一章 对危机的剖析
第二章 建设自由放任的都市
第三章 豪门的西行
第四章 波士顿公园争夺战
第五章 美国东部资金与西部民粹
第六章 变革年代
第七章 结论:转型与再出发
《伟大的转型》作者简介
诺姆·马格尔(Noam Maggor) , 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学博士后和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曾任美国哈佛大学查尔斯·华伦研究中心研究员及美国范德堡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他长期研究美国工业资本主义史、全球化史和美国政治经济学等,尤其关注美国历史上财富精英的管理策略与金融战略。
《伟大的转型》内容简介
在此书中,作者以19世纪下半期的波士顿为场景,以波士顿财富精英为摆脱新英格兰地区以棉花为根基的纺织制造业走向衰落而蓄奴制同时遭到废止带来的经营窘境,而向遥远而广阔的美国西部发起了新的商业征程并成功转型的历史为线索,从美国金融史、商业史、劳工史、家庭史和文化史等多个维度向读者阐释了美国为什么在四十年后能从以棉花为主的农产品出口国转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作者认为这与美国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和金融资本对产业的巨大推动作用分不开。
伟大的转型美国市场一体化和金融的力量截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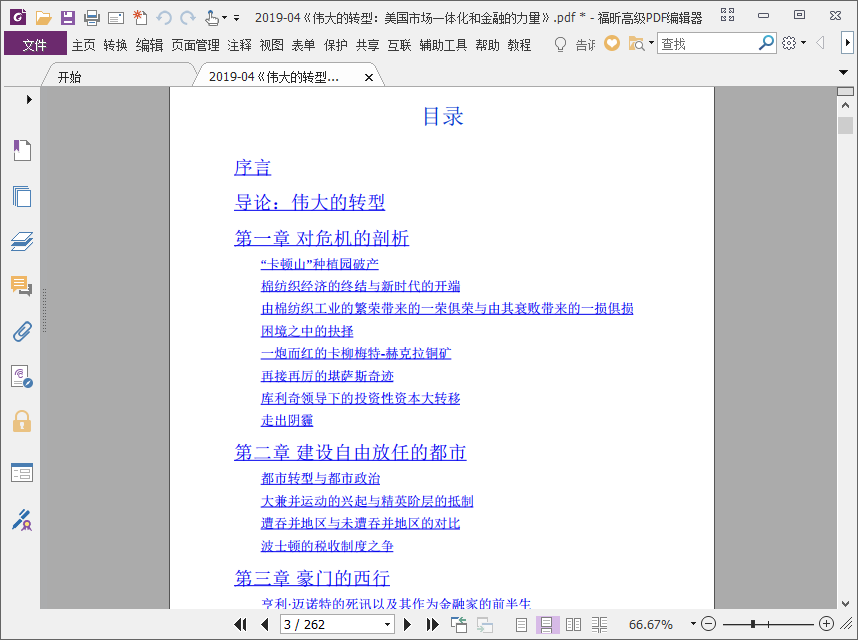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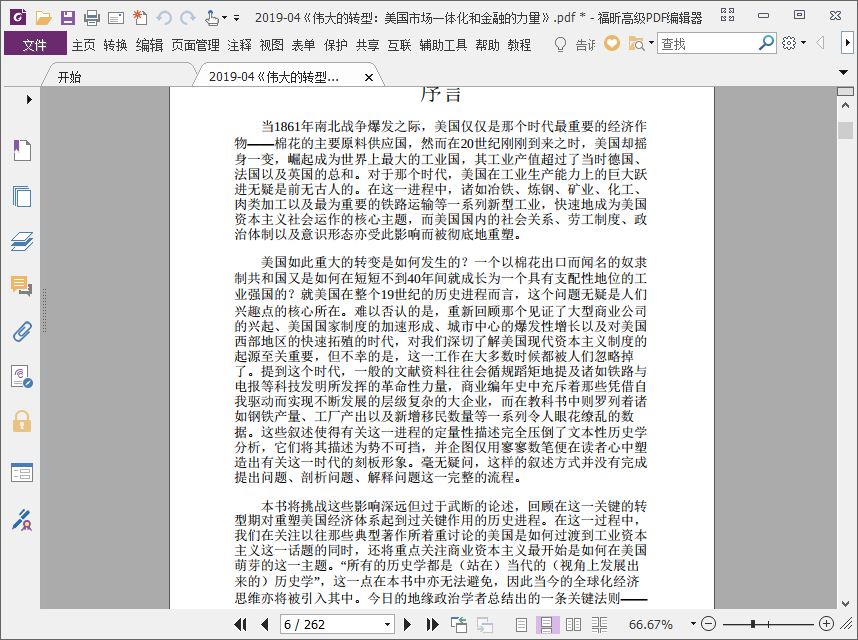
伟大的转型:美国市场一体化和金
融的力量
[美]诺姆·马格尔 著
刘润基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
3
迈诺特的墨西哥中央铁路之行
亨利·迈诺特的死讯以及其作为金融家的前半生
第三章 豪门的西行
波士顿的税收制度之争
遭吞并地区与未遭吞并地区的对比
大兼并运动的兴起与精英阶层的抵制
都市转型与都市政治
第二章 建设自由放任的都市
走出阴霾
库利奇领导下的投资性资本大转移
再接再厉的堪萨斯奇迹
一炮而红的卡柳梅特-赫克拉铜矿
困境之中的抉择
由棉纺织工业的繁荣带来的一荣俱荣与由其衰败带来的一损俱损
棉纺织经济的终结与新时代的开端
“卡顿山”种植园破产
第一章 对危机的剖析
导论:伟大的转型
序言
目录
4
尚未完成的市场一体化进程
第七章 结论:转型与再出发
《特别税务委员会报告》与民粹主义者的反击
小马修斯对都市政治弊端进行分析并提出应对之策
结盟爱尔兰裔选民以及打压统一化公共教育
小马修斯领导下的马萨诸塞州民主党改革
新形势下伊利教授的税改理论
都市财政吃紧背景下来自精英阶层的绝地反击
第六章 变革年代
表象背后的深层动因与制宪会议的最终结果
民粹主义者的进攻与东部代理人的反击
由西部各州的制宪会议而引发的新一轮较力
第五章 美国东部资金与西部民粹
波士顿公园争夺战大结局
精英阶层眼中的“文化等级制度”
技工群体“一切源于劳动”的世界观
精英阶层站不住脚的历史论点
由争端体现出的对立双方世界观的巨大差异
技工与精英阶层的激烈交锋
由技工慈善联合会的请愿引发的争端
第四章 波士顿公园争夺战
波士顿的金融家在美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迈诺特的铁路公司副总裁生涯学会理解复杂的世界
致谢
版权页
5
6
思维亦将被引入其中。今日的地缘政治学者总结出的一条关键法则——
来的)历史学”,这一点在本书中亦无法避免,因此当今的全球化经济
萌芽的这一主题。“所有的历史学都是(站在)当代的(视角上发展出
主义这一话题的同时,还将重点关注商业资本主义最开始是如何在美国
我们在关注以往那些典型著作所着重讨论的美国是如何过渡到工业资本
型期对重塑美国经济体系起到过关键作用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本书将挑战这些影响深远但过于武断的论述,回顾在这一关键的转
提出问题、剖析问题、解释问题这一完整的流程。
造出有关这一时代的刻板形象。毫无疑问,这样的叙述方式并没有完成
分析,它们将其描述为势不可挡,并企图仅用寥寥数笔便在读者心中塑
据。这些叙述使得有关这一进程的定量性描述完全压倒了文本性历史学
如钢铁产量、工厂产出以及新增移民数量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数
我驱动而实现不断发展的层级复杂的大企业,而在教科书中则罗列着诸
电报等科技发明所发挥的革命性力量,商业编年史中充斥着那些凭借自
了。提到这个时代,一般的文献资料往往会循规蹈矩地提及诸如铁路与
起源至关重要,但不幸的是,这一工作在大多数时候都被人们忽略掉
西部地区的快速拓殖的时代,对我们深切了解美国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
的兴起、美国国家制度的加速形成、城市中心的爆发性增长以及对美国
兴趣点的核心所在。难以否认的是,重新回顾那个见证了大型商业公司
业强国的?就美国在整个19世纪的历史进程而言,这个问题无疑是人们
制共和国又是如何在短短不到40年间就成长为一个具有支配性地位的工
美国如此重大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一个以棉花出口而闻名的奴隶
治体制以及意识形态亦受此影响而被彻底地重塑。
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核心主题,而美国国内的社会关系、劳工制度、政
肉类加工以及最为重要的铁路运输等一系列新型工业,快速地成为美国
进无疑是前无古人的。在这一进程中,诸如冶铁、炼钢、矿业、化工、法国以及英国的总和。对于那个时代,美国在工业生产能力上的巨大跃
身一变,崛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其工业产值超过了当时德国、物——棉花的主要原料供应国,然而在20世纪刚刚到来之时,美国却摇
当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之际,美国仅仅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经济作
序言
7
远的地域与边疆并入一个统一的经济实体之中,这样的蓝图远非天衣无
财富和投资的新边界同时也勾画出了社会争论的新边界,将那些遥
济之路。
的老路,而走上了一条崭新的、以美国国内市场为中心的工业型政治经
次运动使美国资本主义的形态脱离了原先那条以大西洋棉花贸易为中心
范围,并将美国西部地区那些刚刚显露头角的企业转变为业界巨擘。这
列商业冒险行为。这一资本的再分配运动极大地拓展了美国农业的覆盖
移,以资本助长了包括铁路运输业、矿业、农业以及畜牧业在内的一系
士顿在内的古老城镇向地处西部地区的那些处于前沿的投资领域不断转
州、怀俄明州以及俄勒冈州那样遥远的目的地。财富从美国东部包括波
投资到诸如密歇根州、堪萨斯州、伊利诺伊州、科罗拉多州、达科他
集他们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棉纺织工业中积累的资本,并把这些资本
资,这将告诉我们那些被称为“波士顿豪门”的富有波士顿精英是如何调
争的结束而从美国东岸的城市中心流向美国广阔的西部地区的资本投
统的国家视角而未被关注。更为关键的是,本书将追踪那些随着南北战
分析,包括城镇、都市、领地以及地区,这些地方性的实体往往由于传
中,我们将对许多发生在那个时代的地方层级上的重要事件进行追踪和
宏观经济学指标或是简简单单的“工业化”一词所详尽描述的。在本书
以肯定的是,这是一段崎岖坎坷且矛盾重重的历程,它绝非可以被任何
迹,而在于探索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版图在19世纪后半叶的转型之路。可
在本书中,我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于追踪美国的国家经济的增长轨
而必须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主题进行探讨。
时,我们亦不能在政治边界的界定这一问题上进行任何想当然的假设,纪横跨整个大陆的国家经济体系是如何形成的”这一充满争议的问题
纷繁复杂的贸易、外交及力量网络之中。同样的,在研究“一个在19世
张,北美原住民史学家则将印第安部落的历史轨迹深深地嵌入到其内部
之中,奴隶史学家追踪着“棉花王国”在美洲大陆上极具侵略性的领土扩
的国家的历史置于更加久远的、通过大西洋与外界互动的整个历史背景
们对于美国19世纪历史的认知:美国建国初期的历史学家便将这个年轻
的。不断更新的、关于政治边界的渗透性及延展性的认识已经改变了我
不断吸收融入世界经济为特色的时代而言,这样的观念也是不合时宜
机,并以大范围资本流动、充满活力的大都市以及美洲大陆的内陆地区
下,这样的观念显然难以适用。同样,对于19世纪后期那样一个充满生
可以当作在其上发生的所有经济行为的承载体,但在当今的全球化体制
在分析问题时,国家往往并非一个合适的单位,尽管在20世纪一个国家
8
写他们的历史,便是本书的主题。
50年代的人能够预料到未来会发生什么,而镀金时代的美国人将如何谱
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不会是命中注定的,几乎没有任何生活在19世纪
的社会团体及社会观点之间的力量并不平衡,其最终产生的结果却无论
力,而要解释这些基础架构的形成则需要从其结果入手。尽管互相竞争
远的影响。只有异常敏捷的手法才能够掩饰那些塑造了基础架构的努
组合在一起,对发展的结果、资源的配置以及财富的分配产生巨大且深
烈斗争。那些创造了市场的政治及法律基础架构可以以多种不同的方式
划,以及他们对在既有政治框架下被默认的规章准则与特权所发起的激
转,而真正导致这些转变最终发生的原因,往往是战略行动者的精心策
现象的发生既非无缝衔接般地接踵而至,也不似时尚潮流那样不可逆
致科学技术的突破或自由市场的建立。事实上,按照革命的逻辑,这些
的争论,向我们展示了即便是大规模的经济转型过程,也并不一定会导
那些围绕着19世纪末期美国国家工业经济的涌现这一现象而爆发出
分化的发展道路。
家行为最终使得美国在各个地方层级上走出了一条更加平均化而非两极
发了那些气势恢宏同时又受到民主制度控制的国家行为,而正是这些国
之上”的都市型工业化社会。这些运动支持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成功地激
力量去创建一个“建立在充分享有包括自由在内的各种权利的劳动阶层
的,因此借由政治的力量便可以重塑经济的形态,他们希望借助民主的
的拥护者却并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眼中,经济形式的转变是由政治驱使
形式的转变是由那些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所导致的,然而这些民粹运动
一种以生产主义为特征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教条指出,经济
域,但尽管如此,在反对愈发集中化的金融力量面前,它们仍然共享了
议事日程绝非整齐划一,它们也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个政党、组织或地
遵从的条款、规则以及所应获得的报酬进行议价。这些民粹主义运动的
论不休时,他们实际是在就自身加入整个国家商业体系的过程中,所应
部地区的定居者围绕着铁路管理、劳工保护以及资源开发这样的问题争
发紧密的城市系统中为自己的家乡争取到最为有利的地位,而当美国西
间的使用等话题展开讨论时,他们的基本出发点是要在一个内部联系愈
趋势的。当城市中的居民围绕着市政预算、城市司法管辖权以及公共空
地区的草根政治运动是如何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去抵制资本集中化这一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揭示那些发生在美国东部城市地区以及西部乡村
关注那些伴随着美国国内市场在不同阶段的发展而激发出的政治争论。
缝,在各种各样的基于区域范围内的讨论中,本书将上下而求索,着重
9
特金森(Edward Atkinson)这位畅所欲言且在利用自由劳力生产棉花方
模的试验,在南北战争尚未结束之时便早已展开。查尔斯向爱德华·阿
Islands),在那里由新英格兰人所领导的以自由劳力替代奴隶的更大规
Morse)则前去拜访了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海岸群岛(the Sea 要9500美元。”而与此同时,另一位合伙人查尔斯·莫尔斯(Charles F. 支持。希金森曾这样向他的父亲提醒道:“钱宁会去拜访您,并向您索
先生被派遣到了波士顿,以期从他们的熟人及家族那里获得坚实的金融
是有备而来的。来自这三人组合之一的钱宁·克拉普(Channing Clapp)
事实证明,为了使自己的道路能够通向最终的成功,这三位合伙人
涌入市场,战后的美国经济终将因此被带上一条繁荣兴盛的发展轨道。
都将一并得到历史的正名,当由此而产出的巨量棉花供给有如潮水一般
兰年轻人的道德情操,还是那些他所坚信的有关市场主义的信仰教条,然不同的道路上发展前行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无论是这位新英格
隶的生产积极性,那么美国的资本主义事业就真的可以在一条与先前截
在,如果物质激励可以代替肉体压迫成功地激发出那些被解放了的前奴
事关重大,如果自由农业方法论相比于奴隶制度的确是更加高级的存
原先由奴隶完成的工作”这一简单问题。[1]
毫无疑问,希金森从事的事业
能够支撑起棉花种植业”这一复杂问题,简化为“自由劳力是否能够胜任
的开始阶段,希金森便相当明智地接受了有关建议,将“自由劳力是否
而一旦这一尝试取得突破,物质财富也必将随之滚滚而来。在这一事业
事业。这无疑是一场发生在社会变革领域与政治经济领域的伟大尝试,建美国棉花种植业”是否具备可行性这一问题,当作了他们为之奋斗的
老兵所组成的团队之中。他们三人结伴同行,并将论证“以自由劳力重
邦军队中光荣退役后,这位出身高贵的波士顿市民便加入了由另外两名
上,一边焦急地探寻着美国资本主义的未来所在。一年前,在亨利从联
1865年9月,亨利·李-希金森一边徒步穿行在佐治亚州的茫茫原野之
“卡顿山”种植园破产
第一章 对危机的剖析
10
至于这些来自波士顿的新老板,尽管他们展示出了一定的善意,但对这
前景远非那样美好。在原先主人的役使下,他们几乎完全拒绝工作,而
然而在那些被解放的奴隶的眼中,这种新型领导机制所能够带来的
到足以购置私有土地的钱。[4]
观收入,还能够帮助这些工人中最勤奋刻苦的那一批人在几年之内积攒
人。希金森希望他们的计划不仅可以为这些工人带来足以维持生计的可
在自己的雇员心中树立起一种有关体力劳动的新观念,并以此来激励工
马、耕犁土地、劈砍干柴并清除杂草。他们寄希望于通过上述种种方式
森的两位助手也加入到了田间劳动者的队伍当中,与工人一起放牧、洗
金森与他的工人一道擦洗地板、粉刷围墙、敲凿铆钉。与此同时,希金
雇工展示劳动背后所蕴藏着的高贵品质。在翻修种植园中的大屋时,希
心的新生活,这三位波士顿人开始使用一种身体力行的方式,向他们的
家畜。为了帮助这群新近获得自由的人更快地适应这种以物质激励为核
在分配给他们的家庭自留地上为自己种植作物,或是饲养鸡或猪等家禽
属可以通过承担种植园中多种多样的工作来取得收入,同时他们还可以
采摘、分类以及加工的棉花重量的多少来获取一份额外的报酬;工人家
的土地面积的大小获得一份基础薪资的同时,他们还可以依照由他们所
为此精心设计了一套契约方案,按照这一方案,在工人按照他们所管理
多困难与挑战中,如何处理好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才是重中之重。希金森
爆发无疑都令这几位来自城市的波士顿人始料未及。而在他们面临的诸
天气状况、异常毒辣的夏季高温以及不合时宜的降雨,这些问题的相继
之路似乎从一开始便历经坎坷。各种各样的棉花病虫灾害、令人郁闷的
尽管这三位年轻人对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充满信心,但他们的创业
60名被解放的奴隶。
几处谷仓。种植园还有专为工人们准备的生活区域,在那里居住着大约
带有一间被美丽的橡树所环绕的宽敞大屋、一台轧棉机、一座磨坊以及
山”(Cottonham)的种植园。这座种植园不仅包括约3万亩的土地,还
下而去,他们最终在位于布赖恩县的森林深处购置了一处名为“卡顿
具备上涨的空间。在制订出这份计划后,他们三人便向着萨凡纳地区南
6000美元[3]
的回报,这一数字本身便已极其诱人,更不要说其在来年还
能够收获14500千克棉花。若真是如此,每个合伙人将能够从中分得
于奴隶,人们过度忽视了肥料的价值),那么他们在第一个季度便至少
商业计划,按照他的预估,只要毫不吝啬地施用肥料(希金森认为相较
至还将手中那充满活力的埃及棉花种子赠予了他。[2]
希金森起草了一份
面拔得头筹的专家进行了咨询,而后者不仅向他传授了丰富的经验,甚
11
渐对一种新的论断深信不疑,若是脱离了持续不断的监视、鞭策、驱驰
为市场激励能够激发劳动热情的理想早已荡然无存。这些波士顿精英逐
们这里得到帮助却丝毫不知感激!”事情闹到了这种地步,原先那种认
取了丰厚的薪水,受到了良好的对待,并获得了悉心的教导,他们从我
一佐治亚创业三人组中,她曾这样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这些黑人领
为了给自己的丈夫提供一种资本主义范式的家庭氛围,她也加入到了这
子艾达是哈佛大学著名博物学家与地质学家路易斯·阿加西斯的女儿,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消沉抑郁的挫败感与歇斯底里的愤怒感。希金森的妻
事情丝毫无差。当初那澎湃的激情与家长式的职责理念早已消磨殆尽,劳资谈判却又重新拉开帷幕,随之而来的一切都与第一个种植季发生的
希金森先前的预期相去甚远。而到了第二个种植季,又一轮令人崩溃的
收成极差又正巧赶上世界棉价的萎靡不振,第一个种植季的产出与
帮互助、同仇敌忾,而这又极大地惹恼了他们的雇主。[7]
礼。当劳工发现就连他们最基本的愿望都遭到了否定时,他们便开始互
望的底线,而为了捍卫这一底线不受侵犯,他们甘愿接受任何风雨的洗
而言无疑是奇异而陌生的,能够长久地居住于自己的小屋当中是他们期
人。”[6]
这种为希金森所抱持的伦理观念,对于那些刚刚获得自由的劳工
那些拒绝工作者的居所,而这些新引进的劳工既可以是白人也可以是黑
工作与挨饿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将从别的地方引入劳工,并用他们挤占
说:“作为在土地上工作的自由劳工,这些获得了解放的前奴隶必须在
园的仓储中获得补给,还将面临遭到驱逐的风险。希金森曾明确地警告
金森赤裸裸地威胁道:如果工人不去挣取薪资,他们不仅将无法从种植
大多数情况下希金森也从未放弃过挥动“市场机制”这一大棒的权利,希
象,一边暗自祈祷能够尽快地获得一批得力的帮手。[5]
尽管如此,在绝
而薪水可以换取食品与衣物”,希金森一边满怀欣喜地观察着上述现
工所喜闻乐见的商品。“这些工人开始逐渐地明白工作可以带来薪水,开始在种植园中售卖诸如印花棉布、法兰绒织物、鞋靴等这些贫穷的劳
三位雇主采取了双重手段,一方面,他们向工人伸出了“胡萝卜”,他们
充塞了那紧随圣诞节而来的种植季。为了赢得工人们的支持与配合,这
为这些波士顿人所支付的薪资严重不足,这直接导致罢工与停工的浪潮
种理想在希金森等人的眼中却无异于痴人说梦。更加要命的是,工人认
英亩地(约240亩)、一匹马”那样的美国梦从未被彻底地放弃过,但这
之中。”事实上,在这些被解放了的前奴隶的心目中,从美国分得“四十
算得上公平。希金森曾这样记述:“他们沉迷于一种将土地平分的执念
由的人曾坚定地认为,只有将这片由他们世代耕作的土地均分给他们才
些前奴隶来说也好不到哪儿去。在这三个人到来之前,这些新近获得自以及系统性的督导,这些获得自由的前奴隶将永远无法可靠地完成工
作。希金森夫人如此坦白道:“这是多么令人失望啊!”[8]
第二个种植季
最终带来了比第一个种植季还要严重的亏损,这也让这几个波士顿人更
加清醒地认识到在当前的情况下从事棉花生产绝非什么有利可图的事
业。在1867年5月底,希金森在收拾了自己的行囊之后打道回府,并在
自己的家乡波士顿,加入了由他的父亲和叔叔开办的、实力雄厚的李-
希金森家族银行,正式地开启了一段即将持续数十年之久的崭新的职业
生涯。
[1]有关发生在“卡顿山”种植园中的实验的描述,参见:Henry Lee Higginson and Bliss Barry, Life and Letters of Henry Lee Higginson (Boston: The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21),247-266; Charles F. Morse, A Sketch of My Life Written for My Children (Cambridge, MA: Privately printed at the Riverside Press, 1927),26-32。这条建议是由希金森的战友弗朗西斯·钱宁·
巴洛将军提供的。有关那个规模庞大,且更为世人所熟知的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岛之上的实验的具体情况,参见:Willie Lee Nichols Rose, Rehearsal for Reconstruction; the Port
Royal Experiment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4); Steven Hahn,A Nation under Our Feet: Black Political Struggles in the Rural South From Slavery to the Great Migration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Eric Foner, Reconstruction: 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1863-1877(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8)。
[2]有关阿特金森是如何提倡这一事业的信息,参见:Edward Atkinson, Cheap Cotton by Free Labor (Boston: A. Williams, 1861)。
[3]根据在DouarTimes网站上的查询,1914年1美元的购买力等同于2018年24.65美元的购买力。——译者注
[4]Higginson and Barry, Life and Letters of Henry Lee Higginson, 254-256.
[5]Ibid., 253,254.
[6]Ibid., 254,252.
[7]Ibid., 264.
[8]Ibid., 262,257, 265.
12
13
荣辱兴衰都已被绑定在了棉纺织工业这条大船上而随之跌宕起伏。棉纺
工,还是那些至关重要的手握城市中富有家族资金储蓄的金融机构,其
域之间的交通动脉、波士顿港口内的商业码头、数以千计的棉纺厂职
建。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新英格兰地区乡间田野上的溪流瀑布、区
铁路、仓储以及那些“连接了生产端、供应端和消费端的港口码头”的修
之中。巨量的金融资源被用于资助修建分布在全美国及全世界范围内的
的土地改良以及与之相关的对工厂建筑、机修工厂以及工人宿舍的修建
计的美元被投入到了围绕着水力磨坊的工厂建设、环绕着新兴工业城镇
工业所产出的丰厚利润则往往又被重新投资于这一行业本身。数以百万
地区修建在溪流旁的水力磨坊进行纺纱纺织”这一事业上,而由棉纺织
中,波士顿的商业领袖们曾将他们的全部财富都押注于“利用新英格兰
样,它也并非一帆风顺或承袭天命的。在南北战争爆发前的半个世纪
贯穿于整个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绝不是简单而线性的,同
新制度”的动因之所在。[1]
资关系以及新式资本主义版图在内的一整套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资本积累
不为人们所注意,但最终“促使棉花经济孕育出包括新兴产业、新型劳
且不可逾越的鸿沟之上架构起了连通的桥梁,并向我们揭示了那个平常
部与西部,整个美国各地区以及都市层级上的发展之间那看似根深蒂固
历史上那充满活力的区际联系。它们在南北战争前后,在美国北部、南
美国的旧城镇中,它们与商业之间有着历久弥新的纠葛羁绊,并凸显出
主义的前行轨迹,也穿插点缀于这段历史之中。这些事迹深深地扎根于
一个重要节点,而类似希金森那样的波士顿人的职业生涯以及美国资本
言,那种尝试在废除奴隶制度后重建棉花种植业的努力,无疑是其中的
极度破碎,且被不同的地域和时间片段划分为无数碎片的漫长历史而
决定性的转折。对于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的那段在人们的意识中
领域开始逐步扩展到政治领域),而美国资本主义的剧目也随之发生了
过程中,来自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北方人逐步退出了(这一撤退从经济
的开端。毫无疑问,繁重的美国南方重建工作正在渐次展开,但在这一
示着美国棉花种植业黄金时代的落幕和一套新型的即将到来的产业秩序
对希金森和他的伙伴而言,发生在卡顿山种植园中的一切似乎正昭
棉纺织经济的终结与新时代的开端织工业逐渐在马萨诸塞及其周边的各州中占据了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它
带来了一种使工业化成为可能的区际联系,而那个在“逐渐走向工业化
的新英格兰地区”与“依靠奴隶从事棉花种植、采摘、轧制的美国农业化
南方地区”之间形成的强大联盟,无疑是这种区际联系的突出代表。[2]
14
图1.1 这是陆军少校亨利·李-希金森身着联邦军制服拍摄的照片,他很快便会成为波士顿最为重
15
冒险之中。
一系列包括矿石开采、畜牧养殖以及铁路建设在内的开天辟地般的创业
们从与棉花相关的领域抽身离去,转而投身于发生在美国西部地区的那
举动当作支撑点,这些波士顿精英开始急剧地拓展自身的商业视野。他
为(尤其是对于那些以刻板和保守而闻名且小有建树的经营者而言)的
化”这一充满雄心壮志的宏图大业。把一系列被当时的人们视作胆大妄
的经济框架进行小修小补,而是瞄向了“在整个大陆范围内推进工业
新构思美国资本主义的未来,这一行为不是为了对那种在早些年间形成
栖身的产业,并以此为出发点走出了一条全新的发展轨迹。他们开始重
展的新途径。就好似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波士顿的市民背离了他们原先
急于打造出资本积累新循环的紧迫感,便催促着人们走上了一条商业发
旗舰产业深陷危机,无法在吸收巨量投资的同时产出足够的利润,那种
前的棉花经济能够重获新生的激情与冲动,亦随之迅速冷却。当原先的
植业新篇章”那样的幻想抛到了九霄云外,那热烈企盼美国南北战争之
开,但包括希金森在内的一群波士顿商业精英,迅速地将“开创棉花种
在美国南方那个曾经的棉花王国的废墟之上,重建工作正在艰难展
可能转变为可能的奴隶制度。
南北战争的结局已经从事实上摧毁掉了那个曾经让大规模棉花种植由不
样,众多的波士顿商业精英仍然幻想着重新点燃棉花经济的火种,哪怕
尝试。正如在前文中提到过的“希金森在佐治亚州进行的大胆冒险”那
波士顿的商业精英义无反顾地不断做出复兴甚至进一步扩张这一产业的
在之前的时代中展现出的那种不断自我激励、自我强化的活力,诱惑着
疑将棉纺织工业继续当作经济增长引擎这一做法的可行性,但棉花产业
失,而整个棉纺织工业也随之经历了一场严峻的危机。尽管人们普遍质
个棉纺织生态。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纺织工厂的盈利能力逐渐流
了商业范畴的广泛根基,也将高度的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能力赋予了整
的发展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为这一进程所倚仗的、延伸范围早已超越
社会的最顶层到最底层)以及整个区域的精神和文化生活都与棉花产业
行政机构、社会组织以及民间机构之中。政府的行为、阶级的分化(从
仅限于经济领域。事实上,这一进程已然深深地扎根于新英格兰地区的
在那个年代,就以棉花为根基的工业化进程而言,其影响范围绝非
(Boston: AtlanticMonthly Press, 1921)
图片来源: Bliss Perry,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Henry Lee Higginson 要的投资银行家这次事关重大的“转向西部”运动影响深远。通过这次转型,波士顿
从原先的区域制造业中心被重塑成了整个美国最为重要的金融中心之
一。在经历了将近十年的停滞之后,这一新兴运动无疑为那些急于寻找
能够产出足够回报的投资标的的资金指明了一条出路,并为那些早已准
备好迎接挑战的波士顿富裕阶层中的年青一代,展示出了一幅宏伟蓝
图。这一运动还极大地增强了波士顿精英对于金融行业的信心,并将一
种全新的使命感赋予那些历史悠久的古老社群。坐落在波士顿州街
(State Street)上的城市商业区,很快便呈现出了一幅熙熙攘攘的繁忙
景象,而在波士顿当地的政治圈中,那种试图探讨“该城应在这一新兴
国家经济实体中扮演何等角色”的争论,也日益甚嚣尘上。而与波士顿
经历的这种种变化同等重要的是,美国那辽阔的西部也开始在来自美国
东部地区的巨额投资的带动下逐渐改头换面。一波又一波闻所未闻、规
模空前的美国东部资本浪潮,以势不可挡之势争先恐后涌入大陆腹地,极大地充实了西部地区的商贸网络。金融家由此获得了对美国原先那种
临时性质的、碎片化的且往往是十分脆弱的产业布局进行重新整合的机
会,而作为这一整合的最终结果,一种在东部城镇中的商业区的统一领
导下,集系统化、稳健化、高度资本聚集化等特征于一身的新型产业布
局应运而生。一系列回报丰厚的新兴产业部门逐渐发展为美国资本主义
的内在核心。最终,依靠一种在政治领域备受争议且在社会领域亦极具
变革性的手段,美国的西部地区及其看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资
源、价值不菲的矿产及农作物一道,被成功地纳入了美国经济的整体大
循环之中。
[1]有关美国南部棉花王国的崛起与北部工业化进程之间的跨越区域的联系,参见:Sven Beckert,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Knopf,2014); Edward E. Baptist,The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 Slaver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Walter Johnson, River of Dark Dreams: Slavery and Empire in the Cotton
Kingdom(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Sven Beckert and Seth Rockman, eds., Slavery’s Capitalism: A New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值得注意的是,奴隶制的消亡与战后美国工业化进程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得到同等级别的关注。
[2]有关这些区际联系的信息,参见:Thomas H. O’Connor, Lords of the Loom,the Cotton Whigs and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 (New York: Scribner, 1968).
16
17
旷神怡的乡村环境之中”,这种工厂运营方式被誉为美国独特的工业化
居住于受到严密监控的宿舍中。“不会永为工薪阶层,且生活在令人心
司操作工厂中的机器,在此期间的若干年中(在她们结婚之前)她们将
劳刻苦的年轻女性构成,她们从新英格兰地区的乡村中被招募至此,专
的20座城市之列。在这座城市中,劳工群体主要是由那些处事干练、勤
州规模第二大的集市城镇,而到1840年,该市更是得以跻身于美国最大
型棉纺织工厂的落成。在这一过程中,原先的乡村田野成长为马萨诸塞
后,发生在这一地区的规模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便带动了多达19处的大
一处落差高达9米的瀑布旁打造一座全新的产业基地。仅仅在不久之
先的创业者在一种更大的野心的驱使下,决定在洛厄尔市梅里马克河中
1822年,受到在沃尔瑟姆市所发生的奇迹般的成功的鼓舞,那些原
原棉被直接加工为成品布料,而这样的创举为人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纺纱到织布的整个棉纺织工业流程都能够在其中完成。在这座工厂中,们创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将上下游完全整合到一起的一体化工厂,从
——的资本投入的资金,作为股本注入到了这一新成立的公司之中。他
章程,而后将十倍于公司的前身——一座位于罗德岛上的小型棉纺厂
瑟姆市的查尔斯河河畔建立起了波士顿制造公司。他们一同制定了公司
和帕特里克·特雷西·杰克逊[4]
的带领下,率先在地处马萨诸塞州的沃尔
格兰地区的商人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团体,在弗朗西斯·卡博特·洛厄尔[3]
上,这一产业在其漫长的生命跨度中往往黯淡无光。1813年,来自新英
极其出彩的开局,往往使人们在对其未来进行预测时产生错觉,事实
疑是对那些棉纺织工业开创者的极佳写照,但由棉纺织工业所展现出的
的发展前景,我们离过度投资还相去甚远。”[2]
这种自信满满的说辞,无
证:“的的确确,大量的资本正被投入这项买卖当中,但面对如此广阔
人实业家内森·阿普尔顿[1]
曾这样向他那满腹狐疑的友人做出了保
夷所思。那时,他们正一股脑地扎进棉花纺织这一产业当中。1821年商
工业而转投于“美国西部大开发”这一事业,还有如天方夜谭一般令人匪
对那些来自波士顿的商人而言,仅仅在数十年前,彻底放弃棉纺织
其衰败带来的一损俱损
由棉纺织工业的繁荣带来的一荣俱荣与由
18
由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和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格党当作自身政治理念的载体,并凭借着该党踔厉风发的领袖集体——
典城”这一梦幻般的标签。最终,这一身为“棉花领主”的核心阶层将辉
士顿这座将自己化身为美国工业革命轴心的伟大城市赢得了“美国的雅
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9]
在内的一批杰出人士,为波
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奥利弗·温德
了足以为那个时代定调的喉舌。包括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家、神学家以及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而把这批人加总在一起,便构成
显赫的民间机构中身居要职。他们资助了一系列杰出的作家、法理学
州总医院、波士顿图书馆、洛厄尔学院以及至关重要的哈佛大学等声名
问,该阶层是整个社会的金主,而这一阶层中的成员亦在包括马萨诸塞
阶层,这一阶层通常聚居在位于比肯山住宅区的典雅寓所之中。毫无疑
时,那些手中握有回报丰厚的股票份额的波士顿人,则结成了一个新的
秀,则跃升为了当地社群乃至整个国家中最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与此同
特·劳伦斯和内森·阿普尔顿那样的成长于乡村而发达于波士顿的后起之
传承悠久的商贸世家,重新树立起了自己的金融及社会形象,而像阿伯
层面、社会层面还是政治层面皆是如此。[8]
如同杰克逊和洛厄尔那样的
群体巩固了自身的地位并牢牢地站稳了脚跟,而这种现象无论是在经济
十家的棉纺厂并雇佣着数以百计的工人。依靠着这样的家底,这一核心
握着多达30家以上的超大型纺织公司,而每一家这样的公司都坐拥着数
里,一个由约80位波士顿市民组成的核心群体便脱颖而出,他们共同掌
这样的产业体系在19世纪40年代达到顶峰。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
分销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7]
着流动资本;而数不胜数的销售代理,则将那产量日益增长的棉纱布匹
变为可能;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为固定资产占比极大的棉纺织工业提供
到位于波士顿的港口;机器制造商组装出各式设备,将大规模纺纱织布
万磅计的原棉运入工厂之中,而后又将出产自这些工厂的成品布料运送
于“波士顿—洛厄尔”“波士顿—伍斯特”那样的区域铁路干线,将数以百
有着紧密的联系)打造出了一套连锁系统。在那个年代,诸多类似
及机器制造在内的各行各业之间(这些行业中的企业普遍与棉纺织工业
广泛存在于企业主阶层之中的凝聚力,他们在包括银行、运输、分销以
多佛以及奇科皮等地在内的整个地区中四处开花的繁荣景象。[6]
依靠着
了棉纺织工业当中,充足的投资造就了棉纺厂在包括曼彻斯特、索科、在随后的20年中,洛厄尔模式的支持者将他们的盈利所得重新投回
模式,向世人不断强调这一模式与美国国家的共和制度相匹配。[5]
19
波士顿最为优秀且明智的精英,他们善于预测,极富科学素养,并精通
划”。[14]
这两座新兴城镇的创立者并不是那些贪得无厌的暴发户,而是
评价的那样,“这是由富有而精明的人们所制定的一项规模宏大的计
作,正如这两个项目的投资者之一威廉·阿普尔顿(WilliamAppleton)
发生在劳伦斯和霍利奥克的一切绝非什么未经深思熟虑的即兴之
方面域追加投入3000万美元到4000万美元资金。[13]
民。而为了充分地利用这两个新近落成的产业基地,人们还将在工厂建
终拥有足以匹敌洛厄尔的庞大人口,并在5年之内入住大约3.3万名居
织机数量将提升大约50%。项目的推行者预计,这两座新兴的城镇将最
装置的水力资源,而当这些纺纱装置最终全部建成时,新英格兰地区的
付出了上述的诸多努力之后,这两个地点获得了足以带动150万个纺纱
拓展了城镇的范围,以容纳更多的教堂、学校、公园以及工人宿舍。在
条宽广的运河,他们同样为该项目建造了最为先进的机器制造工厂,并
便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其中,他们为此修建了一座巨大的堤坝并开凿了一
范围尺度上复制原有成就的努力。早在项目的开始阶段,项目的支持者
目,不但得到了规模空前的庞大资本支持,更代表了人们想要在更大的
为“劳伦斯”,而另一个被命名为“霍利奥克”。发生在这两个地点的项
划,正在两个看似前途光明的地点稳步地推进着,其中一个地点被命名
在那个普遍繁荣的19世纪40年代,企图开启棉花产业发展新阶段的计
近极限,随即棉花产业进入了一种缓慢而线性的扩张阶段。有鉴于此,难。在洛厄尔以及与之相类似的其他地区,人们对水力资源的利用已接
现想要为他们那日益增长的资金池找到合适的投资标的,正变得愈发困
为继的。随着已有的资产不断地产出收益,身处波士顿的投资者渐渐发
然而事与愿违,这一所谓稳固的资本积累策略很快便被证明是难以
运转并持久性地产出稳定红利之上。
(即围绕着棉纺织工业构建起来的商业、社会和政治关系网)可以顺利
赚取钱财。”[12]
毫无疑问,他将自己的期望完全寄托于这一复杂的系统 起来的安全的机器正常运行,我便可以以我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快的速度
来:“对于我来说,只要我的商业智慧足以保障那些由我的叔父所搭建
时,他对自己的前途胸有成竹。阿摩司曾这样向人们解释其信心的由
作为这一宏伟事业的接班人而进行培养,当他于1835年从哈佛大学毕业
漏、万无一失的。年轻的阿摩司·劳伦斯(Amos A. Lawrence)从小便被
入。[11]
在那个时刻,这一紧密编织起来的巨网在世人看来无疑是百无一
议程之中,无论是在州层面还是在联邦层面,他们都有着广泛的介
Webster)[10]
所结成的联盟,成功地将他们的影响力深刻地施加于政务
20
和打击,“绝大多数资产都已被视为毫无价值,而对那些尚有财力物力
个联系紧密的,通常将自己视为谨慎而谦和的投资者群体所造成的困扰
殆尽,而人们的信心则更是如此。”阿摩司尤其注意到,这种恐慌对那
观察到的那样,“现阶段,我们能够从棉纺织工业中赚取的利润已消失
的总市值与原先相比至少蒸发掉了三分之一。[20]
就如阿摩司·劳伦斯所
的企业,其投资价值也早已大不如前。总的概括起来,整个棉纺织工业
整个棉纺织工业中的最大的经销商。就连那些侥幸逃过一劫而免于倒闭
值的40%~60%,共有五家大型公司宣布破产,而其中的两家正是原先
愈发凸显。那些与棉纺织工业相关的股票的市值,大都跌到了其票面价
企业迅速蔓延到整个棉纺织工业时,一直埋藏在这场危机背后的隐患也
掌控着的工业重镇,由此成了历史中的绝响。当倒闭狂潮由最新创办的
为过眼云烟。[19]
这两座规模宏大、经过了精心策划并由波士顿核心团体
克推入了破产清算的深渊,而在这一过程中大约有1000万美元的投资化
于1857年接踵而至的金融恐慌,将早已困顿潦倒的劳伦斯和霍利奥
粉厂、线材厂以及造纸厂一类的规模较小的企业使用。[18]
纺织工厂来此安家落户,便只得以更为低下的费率将土地租赁给诸如面
器所能提供的产能仅得到低效的运用。该项目的业主无法吸引到足够的
在该城镇之中,水力资源的供给远远超过了需求,而那些造价昂贵的机
克计划背后的哈德利福尔斯公司,其糟糕的表现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快便发展到了无法被忽视的地步,而其股价也应声下跌。至于霍利奥
着该公司的股价。[17]
可惜好景不长,这家公司在金融方面所面临的困境
损,但那种弥漫于投资者之间的、对于该项目的坚定信心,坚实地支撑
间,尽管负责建设这一项目的母公司埃塞克斯公司经历着经营上的亏
布机的机械制造工厂,是否真的能够创造价值。[16]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
些为了促进这两座城镇的繁荣兴盛而被建造出来的用于生产纺纱机与织
利润足以让投资者在未来数年之中一无所获。阿普尔顿也同样质疑,那
理位置对于一座工业城镇而言可谓得天独厚,但由产能过剩带来的微薄
泻到了早已饱和的市场当中。阿普尔顿敏锐地察觉到,纵使劳伦斯的地
中的、不可胜数的棉纺工厂全部投入运转时,又有大量的过剩产能被倾
这两座城镇的兴建更是对这一问题火上浇油。当那些坐落在这两座城镇
那个一直存在于棉纺织工业之中的产能过剩问题,而劳伦斯和霍利奥克
免于灾难性的结局。19世纪50年代的早些时候,就连阿普尔顿也看出了
虑后的举动,还是波士顿最富有经验的商人们的督导,都未能让该项目
何对失败的恐惧。[15]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最终无论是那些经过了深谋远
行动是基于最为可靠的商业预测,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他们心中没有任
与重工业及工程施工领域有关的实用知识。这些精英坚信,他们自身的
21
多世纪中,波士顿的商业精英一直坚信,对棉纺厂进行再投资既可以消
这一无解的僵局对于整个区域而言无疑是一个噩耗。在过去的半个
式已丧失了可行的基础,而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
置。[28]
上述建议正式宣告了原先那种推动了地区经济发展的财富积累模
营、巩固现有份额之上,而上马新项目这样的扩张手段则应暂时搁
议这一时期的棉纺织工业制造商应将自身的首要任务放在维持企业运
并对任何企图进一步扩张棉纺织工业的行为表达出明确反对。委员们建
是一种持久性的结构化趋势。该委员会很快便将自己的结论公之于众,们清醒地认识到棉纺织工业的衰退与其说是短暂的偶然现象,倒不如说
乐观态度的人带去了一记重击。在头脑冷静地做出了上述评估之后,人
象,进一步加剧了整个世界市场的饱和态势,并为那些对棉纺织工业持
德国、奥地利、法国以及瑞典等欧陆国家之中的棉纺织工业产能扩张现
有个别公司没能按时分红派息。[27]
雪上加霜的是,同一时期发生在诸如
下降到了1846年的9.7%,而后更是跌至了1859年的5.8%,而在这期间亦
公司的股息率,一直处在衰退之中。这一比率先是从1836年时的11.4%
是做了怎样一件天大的蠢事。”[26]
事实上,那些身处棉纺织行业当中的
数十年中这些公司所摊派的股息红利列出一张清单,就会发现自己究竟
仔细地审视一下这一时期新英格兰地区相关公司的股票价格,并就过去
场对原材料的需求增加,极大地推动了原棉价格的上涨。[25]
“如果我们
上游的原棉生产相对不具弹性,中游纺纱纺织产能迅速扩张而导致的市
格下跌到了所谓的难以赢利的“饥饿点”;而另一方面,由于位于产业链
方面,由于棉纱布匹产能过剩、供大于求,相关产品在下游市场中的价
背景下,那种激进的大规模扩产计划居然还能吸引着人们前去冒险。一
贸易委员会也同样哀叹,纵使在现有工业城镇的棉纺厂产能快速激增的
厂的过度投资”,便是该委员会对这次危机成因的明确论断。[24]
波士顿
创的资产都是由从属于该州的资本所持有的。“对棉纺厂和机械制造工
这次衰退对马萨诸塞州的资本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毕竟,许多遭受重
想。波士顿贸易委员会针对整场危机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并严厉谴责了
棉纺织工业的衰退迫使波士顿的商业精英痛苦地抛弃了原先的幻
居或熟人都已经沦落到了一无所有的境地。[23]
找资金。[22]
阿普尔顿也同样观察到,他的许多曾经自认为十分富有的邻
为艰难的日子里,他每天都在绝望之中为自己那逐渐走向没落的产业寻
陷其中。”[21]
威廉·阿普尔顿也私下承认,在那段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最
这一产业的人们都已沦为乞丐,而不幸的是,许多我最要好的朋友便身
在彼此之间订立合同的人而言,信任感也已经不复存在。许多严重倚赖
22
余的资金流入更加宽广的、以“为棉纺织工业公司与区域性铁路公司的
后,该公司主动缩减了这类贷款的规模,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允许多
然而,这些贷款很快便饱受监管困难以政治争议的困扰,以至于1838年
投入新英格兰地区的乡村田野,并为生活在美国西部的农民发放贷款。
算师便开始为公司寻找替代性的投资出路。他们先是将公司的盈余资金
士顿地区并不能够算得上是十分广阔的市场走向饱和之时,该公司的精
成立于1823年,最初将其资金投入到地产抵押贷款之中,而当这一在波
说,其最主要的存放之地便是“马萨诸塞州医院人寿保险公司”,该公司
线。对于那些最初从波士顿地区海事活动中赚取并积累下来的资金来
与此同时,新英格兰地区的金融机构也遵循了一条相似的战略路
济生态则逐步取而代之。[33]
齐放的经济生态也随之日渐凋敝,而一种以单一和乏味为特色的新型经
关的产业时,那种曾经在新英格兰地区居于主导地位的多姿多彩、百花
额。[32]
当商人逐渐放弃自己原先从事的事业,而投资于与棉纺织工业相
美元的资产,且这些资产在由他所构建出的投资组合中占据了35%的份
19家棉纺织公司以及1家铁路公司中分别持有约合42.8万美元以及12.9万
而转投资到了新英格兰地区的棉纺织经济之中。截止到1851年,库欣在
欣(John Perkins Cushing),也将自己的资本积累从贸易领域中撤出,着30余年在中国广州口岸经营商贸而挣得了巨额财富的约翰·帕金斯·库
家区域性铁路公司中同时身兼股东和董事。[31]
而斯特吉斯的好友,凭借
跟众人一般对棉纺织工业进行了广泛的投资,他至少在6家纺织公司和4
这个从东印度地区的商贸活动中赚取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桶金的商人,也
厄尔、劳伦斯以及索科等地。[30]
威廉·斯特吉斯(William Sturgis)——
的股票以及3家水利公司的股票,而上述的诸多公司则广泛地分布于洛
持股,此外他还购入了2家区域性铁路公司的股票,1家纺织机械制造厂
资领域。到1847年,亨利·李共在多达22家从属于棉纺织工业的公司中
的关税保护机制,但最终也张开双臂拥抱起了棉纺织工业这一新兴的投
贸易商,虽然也曾批判为了扶持本地产业而致使进口商品变得更加昂贵
(Henry Lee)和哈里森·格雷·奥蒂斯(Harrison Gray Otis)那样的资深
投资于区域性铁路公司的行为,也早已成了一种风尚。诸如亨利·李
的波士顿市民而言,那种逐步将自己的资产转移到棉纺织工业当中或是
运输业务从未停息,但即便是对于那些发家、崛起于长途运输行业之中
在更加久远的年代中曾被新英格兰地区的富有阶层当作主营产业的远洋
整个地区的政治经济生态都已牢固地构筑在了上述假设之上。尽管那个
列行为事实上又间接地促进了棉纺织工业的产能扩张)。[29]
久而久之,化掉他们先前赚取的商业利润,又可以从中获取稳定的回报(而这一系
23
(20%)、金融机构(10%)、房地产(13%)以及公用事业(3%)领
资性资产总份额的54%,而在上述的这些资产面前,内森在铁路公司
性地购入这些股票),而这些股票的总估值约83万美元,占据了内森投
总共持有25家棉纺厂及水利公司的股票(内森先生从1813年起开始系统
配置情况中便可窥得一斑。当内森·阿普尔顿于1861年与世长辞时,他
这一点,从诸如亨利·李、斯特吉斯以及库欣等波士顿商业领袖的资产
迅猛崛起导致了其余的工业部门无一例外地失去了大规模资金的青睐,性铁路运输业这一本身便与棉纺织工业水乳交融的行业,棉纺织工业的
种类往往在彼此之间有所不同,但它们无疑同属于一个行业。除了区域
布在不同区域的各式棉纺厂之中,尽管这些棉纺厂所大规模生产的织物
阶层而言,“多样化投资”这一概念往往只意味着将自己的资金投入到分
万名工人,且大部分工人都是女性。[36]
而对于波士顿商业社群中的上流
在新英格兰地区,棉纺织工业成了当地最大的雇主,总共雇佣着多达8
新英格兰地区的棉纺织工业相关资产仍然保有接近7000万美元的估值。
整个产业的危机已经导致该产业的整体市值下降到原先的三分之二,但
共拥有520万台纺纱机以及12.6万台织布机。到了1860年,即便蔓延于
六个州总共拥有380万台纺纱机以及9.3万台织布机,而同一时期美国总
的产值。位于新英格兰地区的六个州主导了棉花纺织这一工业部门,这
四面八方的资本仍在向该产业汇集,且该产业也年复一年地创造出最大
时间节点上,棉纺织工业已经成长为整个美国规模最大的产业,而来自
纺织工业中,该产业的资本聚集程度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那个
到了19世纪50年代末,由于来自波士顿的资本常年稳定地流入到棉
中。[35]
的资金被投放到了那些在马萨诸塞州内部从事经营活动的铁路干线当
公司的总资金池中亦占到了将近一半的份额。同时,还有大约60万美元
美元激增到了接近400万美元,而这些资金在马萨诸塞州医院人寿保险
业相关公司或该行业中的突出人物出面而进行的直接借贷总额,从30万
年到1855年这十年间,以棉纺织工业公司股票为抵押物的,由棉纺织工
司倾向于提供巨额贷款,且其偿还期限通常保持在数年以上。[34]
从1845
(往往期限只有几个月)的商业银行不同,马萨诸塞州医院人寿保险公
织工业一家独大的借款来源。与那些只以适当的资金规模提供短期贷款 路。依靠着上述的经营策略,这家保险公司成功地跃升为了本地区棉纺
圈的核心群体当中开拓出一条十分广阔且还在不断拓宽之中的资金出
进行极为细致的例行甄别的枯燥日常工作之中解脱出来,并在波士顿商
协商安排下,该公司得以将自身从那种负担繁重且需要对各贷款需求方
融资活动进行服务”为宗旨的借贷市场之中。在一种被视为互利互惠的
24
大的纺织工厂的董事会成员名单相互重叠,这些工厂的主要股东几乎全
出了象征权势的堡垒。波士顿图书馆的会员组成与新英格兰地区规模最
赠,[43]
而通过私人领域的资金捐赠,波士顿精英阶层也逐渐为自己构建
育机构之中,这些机构的运转往往有赖于来自波士顿富有市民的捐
类似的集中化倾向同样渗透到了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主要慈善及教
将在棉纺织工业这条大船上风雨同舟。
组合,那么这些从属于不断扩大着的名门望族的成员,便早已命中注定
朋好友。[42]
如果不去考虑这些人各自的专职工作以及他们个性化的投资
导着年度股东大会,同时他们也往往将公司中的重要职位留给自己的亲
阿伯特家族(Abbott)6人。[41]
这些家族利用代理投票的方式持续地主
(Appleton)10人,李家族(Lee)7人,洛厄尔家族(Lowell)7人以及
该公司的初始创办者紧密相连的九大显赫家族,其中共有阿普尔顿家族 克公司于1846年公布的账簿中提及的100个人名中,共有43人从属于与
清楚地向人们展示出,大量的股票是被一群亲族所持有着的。在梅里马
成员之间。在这些公司兼并重组的数十年后,这些公司的股东份额清单
近乎清一色来自新英格兰地区。[40]
事实上,大多数股权转让发生在家族
分之三以上的权益份额大致可以归于约750位股东的名下,而这些股东
究还是有所限定的群体之中。[39]
直到1859年,最大的11家棉纺厂超过四
家、律师、医生以及上述这些人士的女性继承人所组成的规模庞大但终
者不再仅限于其初始发起人,其股东团体便扩散到了一个由商人、实业
人共同开创的企业已拥有了多达400余名股东。当一家公司的股票持有
及。在位于洛厄尔的梅里马克公司成立两年之后,这家由12位初始发起
行股票交易,同时这些股票高昂的票面价值往往也令普通阶层难以企
来源于当地(波士顿地区)。那些富有的股权持有者很少在公开市场进
散至广阔市场之中的匿名投资者之间,同时其所吸取的资本也几乎全部
在那个时代已相当普遍。当然,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权益交割行为尚未扩
在其所有权交割易手的同时保持正常的经营运转,且股权交易这种现象
人物的专利。众所周知,公司制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便是,公司可以
随着时间的推移,持有棉纺厂股票份额这一举动已不再只是那些大
们对其他的产业部门却近乎置若罔闻。
富有的波士顿市民将自己最大的筹码押注在了棉纺织工业上的同时,他
被投资于个人借贷(21%)以及房地产持有(11%)等领域。[38]
在这些
厂,这些资产加总起来占到了他投资组合总份额的67%,其余的部分则
就更加偏重于棉纺织工业了。在1857年时,阿摩司总共投资了17家棉纺
域的投资都显得相形见绌。[37]
至于阿摩司·劳伦斯先生,他的资产组合
25
个地区的广大民众产生深远的影响。
必将急转直下,而这亦将对城市精英、由这些精英所创立的机构以及整
样的背景下,一旦发生在棉纺织工业中的利润萎缩成为现实,经济状况
见的现实便是人们无法找到能够代替棉纺织工业的新型投资标的。在这
取得与棉纺织工业同等规模的经济成果本就十分困难。总之一个显而易
商业精英太多的财力与精力,抑或是因为在其他工业部门中投入技术并
制。[50]
这也许是因为棉纺织工业在数十年中过度迅猛的发展挤占了城市
尔瑟姆—洛厄尔模式”,尚无法在其他制造业领域中被人们成功复
个以“凭借资本高度聚集的工业企业赚取稳定的收益”为核心主题的“沃
在整个运转机制当中,一个贯穿始终却又悬而未决的问题便是,那
社群无法媲美的。[49]
长了波士顿资本家社群的成长壮大,并且其内部强大的凝聚力也是其他
新来者同化到原有群体当中的能力。这样的金融及组织基础,极大地助
展,[48]
这样的现实赋予了精英阶层相同的价值理念,并让他们获得了将
波士顿的商业精英以及那些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民间组织的生存与发
过程,而如今来自棉纺织工业那高度稳定性的涓涓之流坚实地支撑起了
存就如同在风高浪急的海面上行船一般,是一种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
皆捆绑于该产业盈利产出的社会阶层。在久远的过去,财富的积累与留
业已经达到了自身的饱和点时,波士顿早已诞生了一个自身生计与地位
这一切的一切都意味着,当1857年波士顿贸易委员会宣布棉纺织工
济的依赖程度也变得愈发严重。
育、慈善以及社会改良中心的同时,它们对新英格兰地区的棉花纺织经
全地产生收入。[47]
在这些受赠机构依靠着捐款渐渐成长为整个地区的教
快速增加)——被受赠者当成了自有资产一样妥善管理以稳定且十分安
哈佛大学的64万美元(以上捐赠金额仅为1840年记载的数字,其后仍在
波士顿图书馆的15.2万美元、赠予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20万美元、赠予
为建设精英化社会的关键媒介。[46]
这些规模庞大的永久性捐赠——赠予
图书馆及教堂。这些资金改变了学校施教的原有路线,并使该大学转变
了被用来资助学校内法学及神学领域的教职员工,还被用来在校内建造
赠,导致商业利益能够对学校的管理方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私人捐款除
与州政府之间的关系亦渐行渐远。大量涌入的来自波士顿富有市民的捐
会的资助与管控,然而随着19世纪上半叶私人捐赠之风的愈演愈烈,其
佛大学,其原本是作为一所州立大学而被建立,理应受到马萨诸塞州议
该图书馆当时为全美资金最为充裕的非公众图书馆的名声。[44][45]
至于哈
部是波士顿图书馆这一高级俱乐部的会员或捐赠者,而这也最终造就了
26
喜爱,却逐渐地沦为了阶级统治与反动政治的象征。[57]
针对那些“家财
着那种弥漫于哈佛校园之中的贵族做派,这所大学虽然受到精英的由衷
限,甚至身心残缺)之间的、愈发难以逾越的鸿沟,他们还尽情地嘲弄
撮特权阶层与数量庞大的劳苦大众(这些人往往出身低微、教育程度有
背后深深埋藏着的阴暗现实。除了提醒人们特别留意那条横亘在那一小
对立面上,他们毫不留情地向人们揭示出了在这场社会斗争与阶级冲突
(Theodore Parker)[56]
在内的批评家,则旗帜鲜明地站在了辉格党人的
逊(Henry Wilson)[55]
以及这些人中文笔最为犀利的西奥多·帕克 代化社会。而在这场危机的大背景下,包括查尔斯·萨姆纳、亨利·威尔
现社会中所有族群团体的和谐互助为目的、被有效地组织并管理着的现
辉格党人一直在极力鼓吹要建立一种由德才兼备的精英所领导的、以实
作为“工业资本家阶层政治观念载体”的政治势力失去信心。多年以来,秉持家长作风的辉格党人昔日里的旦旦誓言,选民也日益对辉格党这一
波士顿这种江河日下的消极情势,无情地揭穿了那些道貌岸然而又
种使人们逐渐无产阶级化的工业化弊病。
如今再也无法令人们欢欣鼓舞,同时,它还必将无可避免地患上欧洲那
市镇——“一群固化的薪资阶层的窝棚”。那种曾经独树一帜的商业模式
棉纺厂早已褪去了曾经萦绕着其自身的田园气息,堕落为拥挤而肮脏的
的劳工比例不断下降,越来越多的人只得蜗居在狭小的出租屋之中。[54]
尔,就连工人的居住标准也在持续恶化。居住于公司自有的员工宿舍中
的管理者对他们先前曾做出的“为劳工提供良好生活环境”的承诺出尔反
到1850年时的38.6%,而后更是上涨到了1860年时的61.8%。[53]
由于工厂
座典型的棉纺厂中,外来工人所占到的比例先是从1836年时的3.7%激增
之的是一个更加脆弱的移民人群,其中有男人、女人甚至是儿童。在一
年间作为临时劳动力的、出生于本土的女工逐渐在工厂中消失,取而代
的薪水也变得时有时无。[52]
工人的构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些
常态,工人也不再坚守自己的岗位,甚至就连股息的分配与企业管理者
维持工人生计的地步”。随着为了遏制产能过剩现象而展开的停工成为
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劳动力成本被不断挤压,以至于到了一种仅够
同时,工资却停滞不前。工人经历了一波汹涌的失业浪潮。[51]
正如一些
加了至少1倍,而织工也被迫在数倍于原先的织机间往来穿梭。可与此
恶化的生产环境中大负荷地工作——每个工人需要负责的纺纱机数量增
的利润率促使工厂管理者加大了生产环节的强度,导致工人只得在不断
机和政治危机。此时,棉纺织工业早已脱离了其原先的起飞阶段。微薄
了十余年之久的经济萎靡,迅速地发展成了一场影响更加广泛的社会危
为这场灾难火上浇油的是,这场爆发于19世纪50年代的、足足酝酿
27
[6]Ware, 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 142. 这种棉纺织工业内部的连锁反应在相关著作中得到了详细描述: Shlakman, Economic History of a Factory Town, 39-42, 243-
College Studies in History, vol. 20, 1935)。
Profits and Investment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Vera Shlakman, Economic History of a Factory Town; a Study of Chicopee, Massachusetts (Northhampton, MA: Smith Industrial Beginning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31); Spalding, “Promotion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New England”; Paul F. McGouldrick, New England Textil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Origin of Lowell (Lowell, MA: B.H.Penhallow, 1858)。有关这一产业的开端的最为细致的研究,参见:Caroline F. Ware, The 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 A Study in [5]罗伯特·达尔泽尔的记述大致上接受这种乐观的看法,而这与那些创业者在相关著作中表达的自身观点是相一致的,参见:Nathan Appleton,Introduction of the Power Loom, [4]帕特里克·特雷西·杰克逊,美国棉纺织工业先驱。——译者注
[3]弗朗西斯·卡博特·洛厄尔,美国棉纺织工业先驱,完善了现代工厂制度。——译者注
[2]Robert F. Dalzell, Enterprising Elite: The Boston Associate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49.
[1]内森·阿普尔顿,马萨诸塞州纺织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译者注
战争的全面爆发。
运动成功地将妥协这一选项从政治议程中完全移除,并进而促成了南北
敌视态度这两点上,这些运动的参与者却堪称志同道合。[63]
最终,这些
不妥协,以及将那些棉纺织工业巨头视为社会秩序的公敌,并对其采取
地。尽管爆发这些运动的政治诉求与选区千差万别,但在对蓄奴制度毫
动,并最终导致了辉格党在与共和党进行的选战中,接二连三地一败涂
终激发出了包括“自由土地(Free Soil)”[62]
在内的一系列政治反抗运
一个由‘皮鞭之主’与‘织机之主’所结成的邪恶联盟。”[61]
这些口诛笔伐最
贩子,与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厂厂主兼无良奸商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
名的谴责性论断:“路易斯安那州与密西西比州的棉花种植园园主兼人
更是将奴隶问题与精英特权问题放在一起进行思考,并由此而发表了著
这场论战将废奴主义从原先的那种小众议题升级为阶级对立。[60]
萨姆纳
塞州的行政官员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挺身而出,以维护“法律与秩序”。
的棉纺织工业资本家坚定地站在了自己的伙伴身边,他们不断对马萨诸
此而此起彼伏。为了向自己在南方“棉花王国”中的盟友表明忠心,北方
间的裂痕更是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波士顿街头,一系列暴动因
他们原先主人那里”的《逃奴追缉法案》获得通过时,民众与资本家之
视作蓄奴制度的帮凶。而当规定了“应当强制将那些逃亡的奴隶送回到
地。这些北方工业资本家很快便被人们冠以“棉花辉格党”的蔑称,并被
在美国南方的原棉供应者之间的庞大同盟,正逐渐让商业精英名誉扫
萨诸塞州的民众当中深入人心,那个存在于这些北方工业资本家与他们
尽管他们也曾努力抵制这一制度,但从未成功。随着废奴主义逐渐在马
挥之不去的漫漫阴霾。蓄奴制度俨然成了工业资本家最大的政治软肋,此时,围绕着种植园蓄奴制的争论,已悄然发展成了这场危机之中
带来危害。[59]
告道:不断聚集的财富将会给一个工业化的马萨诸塞州原本享有的自由
问。[58]
在对统治阶级以及富人联盟进行口诛笔伐的同时,他们也不忘警
一事实,这些批评家不畏权势,以一种舍我其谁的姿态发出了自己的质
于一切之上的行事方式,以及他们意图为所欲为地操纵摆弄公共机构这
万贯的商业精英”伙同他们“在政治领域内的爪牙”将自身的金融利益置
28
[35]有关马萨诸塞州医院人寿保险公司曾倾尽所能地为马萨诸塞州的农民手上的资金寻找出路的信息,参见:Tamara Plakins Thornton, “ ‘A Great Machine’ or a ‘Beast of Prey’:
Life Insurance Company。
30. 19世纪50年代末发生的大规模亏损并没有见于公司的官方分类账目之中,这一定是由于当时采取了极为激进的会计处理方法,参见:Whit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 Hospital [34]Lance E. Davis, “The New England Textile Mills and the Capital Markets: A Study of Industrial Borrowing 1840-186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 no.1 (March 1960): 1- [33]Moriso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 276.
Larsen, “A China Trader Turns Investor,”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2, no.3 (1934): 345-358。
棉纺织工业的个人或企业。参见:“Schedule of Property,” January 1, 1851, John Perkins Cushing Business Records, Vol.6, Baker Library Historical Collection,Harvard University; Henrietta 大量地产、在波士顿市中心的土地、持有的银行及保险公司中的股票份额、在纽约州北部及宾夕法尼亚州的铁路、政府债券、现钞以及私人借贷,其中的不少借贷都提供给了从事
[32]尽管库欣每年要花费大约5万美元,可谓耗费糜大,但这些投资使他的财富在1831年他从中国返回到1862年他去世时上涨了3倍。其他几处大额资产包括库欣在沃特敦的
[31]Gerald Taylor White, A History of the Massachusetts Hospit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7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123124。
[30]参见:Versa Shlakman, Economic History of a Factory Town, 30; Knneth Wiggins Porter, The Jacksons and the Lees; Two Generations of Massachusetts Merchants, 1765-1844
Merchant and Entrepreneur, 1779-1861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5), 60-61, 110-111, 113。
University Press, 2010),265-267。在内森·阿普尔顿进入国内制造业领域之前,他所从事的事业便是贩卖广东的丝绸和孟加拉的棉花,参见:Frances W. Gregory, Nathan Appleton, 姆斯·劳埃德以及帕特里克·特雷西·杰克逊,参见:James R. Fichter, So Great a Proffit: How the East Indies Trade Transforme Anglo-American Capita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Maritim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 1783-1860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21), 214-215, 225。一些沃尔瑟姆和洛厄尔的初始发起人便是起家于东印度贸易的,包括以色列·桑代克、詹
顿是其位于美洲大陆上的主要目的地,同时波士顿还保持了在整个美国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港口的地位,超过了费城、巴尔的摩以及新奥尔良。参见:Samuel Eliot Morison, The [29]尽管迈向工业化的转型在总体上来说是决绝且只进不退的,但新英格兰人古老的远距离商贸事业从未终止。对于来自东印度群岛、波罗的海及地中海的货物而言,波士
参见:Appleton,Introduction of the Power Loom, and Origin of Lowell.
Press, 1858)。当然,所有人都同意这种低迷将会是长期现象,同时整个体系的结构急需改革。内森·阿普尔顿撰写了辩解书,咬定这次衰落是由小规模生产者的过度竞争引起的,样也有一些详尽描述舞弊与渎职的案例,参见:Report of the Investigating Committee to the Stockholders of the Bay State Mills at Their Meeting, February 5, 1858 (Boston:J. H. Eastburn’s 中化之害,导致了管理上的疏失。参见:James C.Ayer, Some of the Uses and Abuses in the Management of Our Manufacturing Corporations (Lowell, MA: C. M. Langley Co., 1863)。同
话与这场危机的根源相关,比奇洛认为现在的困境证明了公司这种形式与制造业并不相称,而另一位畅所欲言的评论家詹姆斯·艾尔则提出,整个产业遭受到了裙带关系及过度集
Remarks on the Depressed Condition of Manufactures in Massachusetts: With Suggestions as to Its Cause and Its Remedy (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 1858), 23, 17。有一段十分生动的对
[28]Boston Board of Trade, Annual Report, 1858, 54. 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结论。有关资本家不愿继续投资,同时积极地回避整个制造业的情况,参见:Erastus B. Bigelow,分红了。”参见:Joseph G. Martin, Twenty-one Years in the Boston Stock Market, Or, Fluctua-tions Therein: From January 1, 1835 to January 1, 1856 (Boston: Redding and Co., 1856), 42。
多,而多数股东继续持有这类股票的力度仍很强大,这类股票继续贬值的趋势无疑得到了缓和。尤其是考虑到许多这类股票早已不是错过了一到两次的分红,而是连续错过了六次
——“我们所听到的有关这类股票遭遇巨大损失的消息还算不上多,尽管许多这类面值为1美元的股票售价已经跌破了75美分甚至50美分,但由于被真正投入到市场中的股票并不
造类股票的衰落在19世纪50年代的波士顿是众所周知的。而波士顿股票市场的编年史记述者也同样注意到,由于大量股票的交易很不活跃,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遭到了掩盖
势,其资本回报率的平均水平在1830—1834年为10.3%;1835—1839年为9.4%;1840—1844年为6.8%;1845—1849年为12%;1850—1854年为6.1%;而在1855—1859年则为6%。制
32, no.2 (June 1958): 209。大卫检验的九家公司(Amoskeag,Dwight, Cabot, Perkins, Hamilton, Lancaster, Lawrence, Lyman, and Massachusetts)全都显示出了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的态
[27]参见:Ware, 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 113, 151, 153; Lance Edwin Davis, “Stock Ownership in the Early New England Textile Industry,”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26]Boston Board of Trade, Annual Report, 1858, 53-54.
[25]Boston Board of Trade, Annual Report, 1859, 165.
Boston Board of Trade, Annual Report (Boston:Press of George C. Rand and Avery, 1858), 53。
[24]Boston Board of Trade, Annual Report (Boston: Press of George C. Rand and Avery, 1859), 165. 中等级棉花的价格从1843年时的6.25美分上涨到了1857年时的16美分,参见:
Amos A.Lawrence Papers, Box 11, September 1857, MHS.
他还记述道:“可敬的阿伯特·劳伦斯先生损失了大概100万美元,而阿摩司·劳伦斯先生的投资组合则下跌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市值,从45.3万美元缩水到了约29.4万美元。”参见:
[23]尽管相比于自己的邻居,威廉·阿普尔顿的损失并没有那样惨重,但按照他本人的估算,他所持有的制造业股票的总市值从大约60万美元下跌到了大约40万美元。此外,[22]Entries on September 25 and October 1, 1857, in Appleton, Selections from the Diaries of William Appleton.
[21]A. A. Lawrence, Letterbook, October 19, 1857,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MHS).
1859), 163。有关经济萧条的信息,参见:Spalding,“Promotion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New England,” 210。
[20]“股份制公司的股价从没有那么低过,而制造业资产似乎已不具任何价值。”——参见:Boston Board of Trade, Annual Report (Boston: Press of George C. Rand and Avery,1987)。
[19]想要更广泛地了解有关1857年金融恐慌的信息,参见:James L. Huston,The Panic of 1857 and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8]Cole, Immigrant City; Green, Holyoke, Massachusetts.
们不再制造麻烦,参见:Spalding, “Promotion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New England,” 195, 197-198, 209-210。
[17]据说,在一场极为热烈的股东大会上,阿伯特·劳伦斯曾发表了一个小时的长篇大论(也许是不想让他人讲话),并使用极为高超的技巧平息了股权持有者的激愤,令他
[16]December 1, 1885, in Appleton, Selections from the Diaries of William Appleton, 180.
199。
艾德蒙德·德怀特、詹姆斯·米尔斯、萨缪尔·埃利奥特、帕特里克·特雷西·杰克逊、托马斯·帕金斯以及乔治·莱曼,参见:Spalding,“Promotion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New England,” 帕金斯以及萨缪尔·劳伦斯,参见:Hamilton Andrews Hill, Memoir of Abbott Lawrence (Cambridge, MA:Privately Printed at John Wilson and Son, 1883), 24-25。霍利奥克的投资者包括
[15]这些投资者中包含波士顿顶级的商业精英,包括约翰·阿莫里·洛厄尔、威廉·斯特吉斯、内森·阿普尔顿、乔治·莱曼、帕特里克·特雷西·杰克逊、詹姆斯·劳伦斯、托马斯·
[14]William Appleton, Selections from the Diaries of William Appleton, 1786-1862,ed. Susan Mason Lawrence Loring (Boston: Merrymount Press, 1922).
England,” 180-184, 199-209.
[13]Donald B. Cole, Immigrant City: Lawrence, Massachusetts, 1845-1921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3); Spalding, “Promotion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New
[12]William Lawrence, Life of Amos A. Lawrence: With Extracts from His Diaryand Corresponden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888).
Establishment: Upper Strata in Boston, New York, Charleston, Chicago, and Los Angeles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2).
1982); Ronald Story, The Forging of an Aristocracy:Harvard the Boston Upper Class, 1800-1870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0); Frederic Cople Jaher, The Urban [11]Peter Dobkin Hall,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1700-1900: Private Institutions, Elites,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National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任美国参议员。——译者注
[10]爱德华·埃弗里特,美国政治家,曾任马萨诸塞州州长、哈佛大学校长和美国国务卿;韦伯斯特,美国著名的政治家、法学家和律师,曾三次担任美国国务卿,并长期担
国著名法学家,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译者注。
[9]约瑟夫·斯托里,1811—1845年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朗费罗,翻译家,被全世界视为美国最伟大的诗人;霍尔姆斯,美国诗人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之子,他是美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1992), 221; Robert Brooke Zevin, “The Growth of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after 1815,” in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ed.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New Atlantic Slave Trade: Effects on Economies, Societies and Peoples in Africa, the Americas, and Europe, ed. Joseph E. Inikori and Stanley L. Engerma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8]Dalzell, Enterprising Elite, 79, 233-238; Ronald Bailey, “The Slave(ry) Trad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New England,” in The
[7]大约三分之一的成品被运往了美国南部,而另外的10%被出口到了巴西、智利乃至中国等地(出口量逐渐增加),参见:Ware, 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
247; Spalding, “Promotion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New England,” 87-88, 102, 107, 126, 127, 139。A Boston Corporation and Its Rural Debtors in an Age of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27, no.4(2007): 567-597。不出所料,棉纺织工业中的领导人物在随后的
几年中取得了公司的控制权。弗朗西斯·洛厄尔,作为波士顿制造公司创始人之子,成了马萨诸塞州医院人寿保险公司的精算师。阿摩司·劳伦斯、阿伯特·劳伦斯以及内森·阿普尔
顿则成了公司财务委员会的成员。仅仅是靠着极为激进的会计处理方式,该公司的名誉才得以在1857年危机爆发之后继续保持,参见:“Appendix to Actuary Report,” December 28,1857,AA-1 Case 1, 1823-1956, in Massachusetts Hospital Life Insurance Co., Baker Library Historical Collec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36]大约有3万名男性和5.15万名女性,参见:Manufactur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860, ix-x, lxxiii。
[37]Gregory, Nathan Appleton, Merchant and Entrepreneur, 197-198, 271.
[38]Amos A. Lawrence Papers, Box 11, September 1857, MHS.
[39]截至1842年,精确的数字是总共有390名不同的持有者。超过90%的绝大部分的股票都是由商人、地产信托、律师、工厂主、医生、文学机构、妇女(一般而言是前几类
人士的遗孀或女儿)以及那些从商界退休的人士所持有。农民及普通职员拥有的股票不超过总份额的7%,参见:Ware,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到了1859年时,整个
产业的股票中大约四分之一的份额是由女性继承人及地产信托持有的,参见:Davis,“Stock Ownership in the Early New England Textile Industry,” 216,218。
[40]在这段时期,波士顿的总人口达到了接近18万,参见:Ware, 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 Davis, “Stock Ownership in the Early New England Textile Industry”;
Zevin, “The Growth of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after 1815,” 294-295。
[41]Ware, 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 149-150.
[42]Ayer, Uses and Abuses in the Management of Our Manufacturing, 4.
[43]Hall,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72, 110.
[44]1852年波士顿市政议会通过立法使其成为公众图书馆。——译者注
[45]Dalzell, Enterprising Elite, 124-125; Ronald Story, “Class and Culture in Boston: The Athenaeum, 1807-1860,” American Quarterly 27, no.2 (May 1,1975): 178-199. 刨除掉房地产及
大量的文献及美术收藏,它所捐赠的“生产性资产”价值便高达15.2万美元。
[46]Story, The Forging of an Aristocracy.
[47]Dalzell, Enterprising Elite, 159-160. Seymour Edwin Harris, Economics of Harvard, Economics Handbook Serie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0), 368.
[48]我个人对于商业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本质上的不同理解来自皮埃尔·瑞尔威针对这一主题的权威著作,参见:Pierre Gervais, “A Merchant or a French Atlantic?
Eighteenth-Century Account Books as Narratives of a Transnational Merchant Political Economy,” French History 25, no.1 (March 1,2011): 28-47; Pierre Gervais, Yannick Lemarchand, and
Dominique Margairaz,eds., Merchants and Profit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680-1830 (London:Pickering and Chatto, 2014)。
[49]有关美国国内大资产阶级沆瀣一气的文学著作也认同这一观点,参见:Jaher, The Urban Establishment; Seven Beckert, The Monied Metropolis:New York City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American Bourgeoisie, 1850-1896(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Betty Farrell, Elite Families:Class and Power in Nineteenth-Century Bost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50]马萨诸塞州的第二大产业——鞋靴制造业是由数以百计资本匮乏的企业构成的,就如同这一时期其他类别的制造业一样,它们是靠着小企业主的私人借贷来获得融资
的,参见:Alan Dawley, Class and Community: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Lyn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有关更广泛的大型金融机构与制造业投资之间的联
系不畅的信息,参见:Glenn Porter et al.,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Studies in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Nineteenth-Century Marketing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1)。大卫同
样观察到,如果抛开棉纺织工业和铁路运输业不谈,那么私募债券总体而言是不为人们所知晓的。政府债券往往无利可图,且有时甚至并不安全。参见:Davis, “Stock Ownership
in the Early New England Textile Industry,” 209。
[51]Thomas Dublin, Women at Work: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 and Community in Lowell, Massachusetts, 1826-18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 137; Laurence F.
Gross, The Course of Industrial Decline: The Boott Cotton Mills of Lowell, Massachusetts, 1835-1955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63.
[52]Ayer, Uses and Abuses in the Massachusetts of Our Manufacturing.
[53]从1836年到1860年,在位于洛厄尔的汉密尔顿公司中,本地出生的女工数量从737名锐减到了324名,参见:Dublin, Women at Work, 138; Vera Shlakman, Economic History
of a Factory Town, 138-150。
[54]在汉密尔顿公司中,居住在寄宿公寓中的工人比重从1836年时的四分之三减少到了1860年时的三分之一,参见:Ware, 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 4; Dublin,Women at Work, 138-139, 140-141; Gross, The Course of Industrial Decline, 24。在布特公司中,工人群体的文盲比例有所上升,从1838年时的11%上升到了1876年时的25%,参见:
ibid., 63。
[55]亨利·威尔逊,反对奴隶制度,脱离辉格党后筹建共和党,南北战争后积极帮助为黑人建立完整的政治、民权措施。曾任联邦参议员,1872年在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
政府任副总统。——译者注
[56]美国废奴主义者,曾为逃跑奴隶提供帮助。——译者注
[57]Sven Beckert and Katherine Stevens, Harvard and Slavery: Seeking a Forgotten History (Cambridge, MA: Privately printed, 2001); Craig Steven Wilder, Ebony Ivy: Race, Slavery,and the Troubled History of America’s Universities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13); Samuel Eliot Morison, Three Centuries of Harvard, 1636-193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287.
[58]William F. Hartford, Money, Morals, and Politics: Massachusetts in the Age of the Boston Associates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1).
[59]“The Danger That Threaten the Rights of Man in America” (July 2, 1854) an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Theodore Parker, ed. Frances Power Cobbe (London:Trubner, 1863), vol.1, 257,vol.6, 141. 有关经济民粹主义与废奴主义之间的交互关系,参见:Dean Grodzins, “ ‘Slave Law’ versus ‘Lynch Law’ in Boston: Benjamin Robbins Curtis, Theodore Parker, and the Fugitive
Slave Crisis, 1850-1855,”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Review 12 (January 1, 2010):1-33; Dean Grodzins, “Theodore Parker and the 28th Congregational Society:The Reform Church and the
Spirituality of Reformers in Boston, 1845-1859,”in The Transient and Permanent: The Transcendentalist Movement and Its Contexts, ed. Charles Capper, Conrad Edick Wright, and Austin
Bearse (Boston: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1999), 73-117。
[60]Grodzins, “ ‘Slave Law’ versus ‘Lynch Law’ in Boston.”
[61]Charles Sumner, The Works of Charles Sumner (Boston: Lee and Shepard,1870), vol.2, 81. 马萨诸塞州中的草根反对运动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但在19世纪早期,这些运动被
成功地控制住了,参见:Andrew R. L.Cayton, “The Fragmentation of ‘A Great Family’: The Panic of 1819 and the Rise of the Middling Interest in Boston, 1818-1822,”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2, no.2 (1982): 143-167; Harlow W. Sheidley, Sectional Nationalism:Massachusetts Conservative Leade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 18151836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8)。
[62]即自由土地党,一个曾经于1848—1852年美国大选中存在过的政党,反对将蓄奴制度引入美国的西部地区。——译者注
[63]Hartford, Money, Morals, and Politics; Steven Taylor, “Progressive Nativism: The Know-Nothing Party in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Journal of Massachusetts 28 (2000), 167-184;
John R. Mulkern, The Know-Nothing Party in Massachusetts: The Rise and Fall of a People’s Movement, New England Studies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0); Dale
Baum,“Know-Nothing and the Republican Majority in Massachusetts: The Political Realignment of the 1850s,”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4, no.4 (1978):959-986; William Gleason
Bean, “Party Transformation in Massachuset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ntecedents of Republicanism, 1848-1860” (Ph. D.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22).
29
30
过三代将成必然……但这样的手段极为少见,更鲜有成功”。[1]
发展的自然规律,“除非采取某些非常手段以抑制这一进程,否则富不
护自身地位的阶层,都终将无法免于衰败的结局,而这种命运正是事物
利弗博士明确地断言,任何像他们那种靠着商业利润而非贵族特权来维
葡萄酒,他们总是佩戴着洁白的假发并穿着饰有丝质流苏的长靴”。奥
在银制火锅中煮熟的鹿肉并畅饮从精心雕琢的器皿中取出的冰镇马德拉
成了腐化的绅士,“他们整日忙于驾驶自己的豪华马车四处游荡、享用
的行文基调掩盖住了作者内心焦虑的小说之中,这些年轻的贵族被恶搞
品质的无能之辈。在由奥利弗博士所著的那部脍炙人口的、以诙谐幽默
的观察体会时,形容这些年轻人是既缺乏阳刚之气又不具备高贵的勇敢
弗·温德尔·霍尔姆斯博士,在谈到他对年青一代毫无英雄气概这一特点
起过同时代观察家的信心。身兼执业医师和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的奥利
一代的肩上。然而,这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年青一代,却几乎从没有唤
而逐渐逝去或淡出,构建新型经济政治策略的重担便猛然落在了年青新
当新英格兰地区早年间工业化进程的总设计师,伴随着危机的加剧
万劫不复。
南方蓄奴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与卫道士,在道德领域他们更是百口莫辩、尊敬的个体的形象,也不可避免地一溃千里。更加糟糕的是,作为美国
投票给他们了。而最终,这些精英作为公众利益代言人以及社区中最受
赞美和传播,此时此刻亦显得空洞无比,新英格兰地区的选民再也不会
破碎,他们原先对于在自己治下所实现的“跨阶级和谐”与“英明治理”的
破坏性的。每一场竞选过后,这些大资产阶级所倚赖的政治载体便愈显
在看来其也不能例外,而对大量贫困的工薪家庭而言,这个进程是极具
作欧洲工业化进程的对立面,人们曾经认为这一进程温和而有益,但现
别提恢复到原先那种自我扩张的态势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曾一度被视
立起来的棉纺织工业体系,现已步履维艰,连产出利润都做不到,就更
一种四面楚歌般的悲惨境地。那个由他们煞费苦心地惨淡经营才最终建
击,19世纪50年代时波士顿曾风光无限的资产阶级,事实上已经陷入了
遭受着来自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的全方位打
困境之中的抉择
31
立联系——这一点同样重要,因为在阿摩司接下来数十年的职业生涯
英格兰地区出产的纺织产品打开销路;二来便是要与当地的精英阶层建
征程。他此行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来是要招徕当地的批发商贩,为新
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亲笔书写的推荐信件,踏上了前往美国南部的
方式。而在不久之后,劳伦斯便携带着由他的叔叔——一位在南方地区
过在城镇中几座棉纺厂内的学习实践,他了解并掌握了纺织工厂的运作
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商人,他的第一站就是棉纺织重镇洛厄尔,通
劳伦斯和美国南方的紧密联系早在其职业生涯的初期便已然建立。
劳伦斯在棉纺织工业中身居要津。[4]
斯筹措经营资金时的借贷来源。这些复杂的业务关系奠定了小阿摩司·
萨诸塞州医院人寿保险公司董事会中的董事,而这些机构又往往是劳伦
与此同时,他还是一家商业银行、一家保险公司以及前文中所提到的马
例,在由劳伦斯自己开办的公司当中,他既是财务总管又是公司总裁,而劳伦斯家族本身又是柯钦科公司的大股东之一。按照约定俗成的惯
斯公司”,并与“萨蒙福尔斯镇柯钦科公司”签订了排他性的代销协议,中经历过一段学徒生涯。[3]
1843年,他创办了作为专卖商的“梅森-劳伦
立事业而正式成为一名代销商之前,劳伦斯曾在由他叔父所承办的公司
让的继任者,也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一尝试的领军人物。在开启自身的独
儿子、阿伯特的侄子以及威廉·阿普尔顿的女婿,是棉纺织工业当仁不
业兴许就能触底反弹、东山再起。[2]
小阿摩司·劳伦斯,作为大阿摩司的
家当中的生产规模,并由此推动新一轮的关税保护,这样一来棉纺织工
他们希望通过与南方种植园主达成新的妥协来扩大棉花种植业在整个国
冲突爆发的保守人士而言,那种因循旧例式的应对之策显然更受青睐。
对于那些深深根植于棉纺织工业、近乎绝望地想要维持现状并避免
然不同的方向发展下去。
问,这两条背道而驰的路线将令波士顿乃至整个美国的资本主义向着截
营,挽救自身的名誉,并努力打造出一套全新的经济运行秩序。毫无疑
了坚守现状而进行的斗争当中;另一条则是主动加入废奴主义者的阵
条出路可供他们选择:一条是背水一战,将自己的全部身家都投入到为
他们也只能张开双臂拥抱挑战了。事实上,在这场危机之中大致只有两
自身前景的悲观预言以及他们所处的阶级那近在眼前的坍塌崩落之时,在忧郁地寻找着自身的出路。可尽管如此,当他们面对着那些有关他们
机爆发期间的大多数时段中,这些年轻人都显得意志消沉,他们基本都
倒”般的巨大潜力,尚不为人们所知。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危
在那个年代,潜藏在这群新一代的年轻人背后的那种“挽狂澜于即
32
与南方棉花种植园园主之间的联盟置于其他一切之上的使命感,让劳伦
制度为条件换取在堪萨斯州中实现废奴。[9]
一种将北方棉纺织工厂厂主
权威并安抚那些南部人士,劳伦斯提出以准许在新成立的州中施行蓄奴
者,在发生于堪萨斯州的冲突中逐渐占据上风时,为了维护联邦政府的
遣美国司法警察对废奴主义者采取强制行动。[8]
当支持奴隶制的殖民
得自由的黑人从法院中营救劫走后,劳伦斯在极度震惊之中更是要求派
叫沙德拉·敏金斯(Shadrach Minkins)的被抓获的逃亡奴隶,被一群获
升级时,以劳伦斯为代表的骑墙派被推入了窘境。而在1851年,一个名
街头与堪萨斯州中为了抵制《逃奴追缉法案》而爆发的暴动和抗议逐渐
使用和平的法律途径将奴隶制从堪萨斯州彻底根除。然而,当在波士顿
在幕后支持、资助了“新英格兰移民援助协会”的活动——该组织致力于
能游刃有余。对争议双方在1850年达成的妥协,他表示赞同,同时他还
始,凭借着这种中立而温和的身份定位,劳伦斯在行为处事的过程中尚
潜在风险,并将任何可能会导致严重对立的政策扼杀于襁褓之中。一开
不偏向身陷于奴隶制争端之中的任意一方,他寻求的仅仅是提前预知到
提。劳伦斯将自己定位为头脑精明、行事冷静的务实主义者,因此他并
认识到,棉纺织工业的繁荣与长久必须以廉价而可靠的原棉供应为前
植业和北方棉纺织工业之间的合作关系)的隐患都异常敏感。他清醒地
密无间的伙伴关系,导致他对任何可能威胁到区际合作(指南方棉花种
劳伦斯作为棉纺织制造商,以及他与南方种植园园主建立的那种亲
斯长久以来一直憧憬着的生意伙伴。
地区的来客,他们礼尚往来、充满善意,[7]
而这样的交往对象正是劳伦
管理者以及市镇中的商人,是与其意气相投的正人君子。对于新英格兰
着的伟大进程。劳伦斯很快便发现,当地的东道主——棉花种植园中的
壮丽的建筑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昭示着在这座不断崛起的城市中正在发生
表赞赏,同时他也注意到了城市中富丽堂皇的圣查尔斯酒店,这座宏伟
新奥尔良市中的那种倡导应以四海为家的法式浪漫主义情怀,劳伦斯深
相反,他最关心的是脚下这片广阔而欠缺开发的南部疆土。对于弥漫在
存在以及奴隶遭到肆意贩卖的客观事实并没有引起劳伦斯的过度注意,车,亦在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的州界上往来穿梭。[6]
奴隶制的现实
成捆的棉花被堆放得到处都是,而满载着身为黑奴的妇女与儿童的囚
印第安人袭击所留下的痕迹。他看到在不久前才刚刚被殖民的土地上,上,劳伦斯亲身体会到了发生在那一时期的土地投机热潮,观察到了由
穿行在1836年时的路易斯维尔、纳什维尔以及蒙哥马利的茫茫原野之
后的几次与之相似的远征,劳伦斯得以观察到快速拓展着的南部边疆。
中,他将与这些南方精英唇齿相依、同舟共济。[5]
借着这次旅行以及随
33
变过程中,这些年轻人清楚地感受到了原先曾经和睦的南北方关系逐渐
际,该群体中的年青一代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在这一令人震惊的心理转
制度产生冲击的新生思想心怀芥蒂,然而在19世纪50年代行将结束之
波士顿的上流社会一直对诸如废奴主义那类可能使人头脑发热并对现行
年青一代波士顿精英,则采取了一套截然不同的应对之策。长久以来,与劳伦斯的所作所为背道而驰的是,那些与棉纺织工业牵扯较少的
的联系并进行共同的努力。
事实上,直至南北战争的第一枪打响,该组织的成员之间还保持着密切
着与南方达成新一轮妥协方案的诉求,他们还曾向华盛顿发起进军。[16]
有违宪法的“个人自由法案”,都遭到了这一组织的残酷打压。最终,带
织,而无论是被他们视作大逆不道的“废奴主义会议”,还是被他们看成
伦斯还与一些前辉格党人一道组建起了“波士顿联邦储蓄委员会”这一组
甚至在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5]
当选了美国总统之后,劳
衷于追随“自由贸易”的风潮,而并不理会保护美国国内市场的提议。[14]
界范围内原棉需求的持续扩张而导致的价格提升,致使当地人民更加热
寥寥。北方民众将其视为陈腐过时的荒谬提案,而在美国南部,由于世
错愕的是,劳伦斯的种种努力不仅在北方毫无进展,就连在南方也应者
够让原先那种支撑了美国棉花经济的联盟模式重获新生。[13]
可令人感到
国规模最大且产生了最多收益的产业)相关的保护政策,他希望由此能
岸。劳伦斯对自己所在的党派施压,要求其尽力推进与棉纺织工业(美
义策略。按照这一策略,蓄奴区将一直延伸到密苏里线以南的太平洋沿
对开拓西部的忌讳,同时他也拥抱起了该党在对待奴隶制方面的绥靖主
凭借“冷静的头脑”对抗“狂热的冲动”为宗旨。劳伦斯收回了他早些年间
选人参加竞选,后者是一个极富代表性的美国政党,以坚守美国宪法、图重掌舆情。他曾先后于1858年和1859年作为美国党和立宪联邦党的候
在南北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劳伦斯曾花费了两年时间不屈不挠地力
来什么呢?”[12]
州的崩坏衰落以及这些州中优秀儿女的流离失所之外,这究竟还能够带
与白人实现平等,究竟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除了会导致美国南方各
劳伦斯坦白道:“我实在无法理解将600万黑奴解放,并让他们在政治上
运动上走极端,并将个人观点凌驾于宪法之上”。[11]
在自己的日记中,Andrew)这位马萨诸塞州的州长先生,劳伦斯则认为“此人喜欢在废奴
纳评价为“反对蓄奴制度的偏执狂”,而至于约翰·安德鲁(John
将约翰·布朗(John Brown)[10]
诋毁为“毫无爱国之心的大骗子”,将萨姆
斯最终走上了一条同情南部价值观并将废奴主义者视为死敌的道路。他
34
着中心地位,并经常从事与棉纺织公司相关的股票交易活动,但希金森
族一同长大。尽管由他父亲所经营的经纪人事务所在波士顿州街上占据
的新英格兰商人家庭中,而后在比肯山的居民区里,他与自己的远房亲
就斐然的投资银行家。1834年,希金森出生在一个传承悠久且人脉广泛
李-希金森,似乎生来便注定将成为南北战争后波士顿工商业秩序中成
的精英家族。在前文中所提到的发生在卡顿山的故事中的主人公亨利·
济秩序发展方向的杰出领袖,大多来自那些与棉纺织工业少有直接关联
那些在南北战争结束后开始显露头角的、决定了美国新型政治及经
邦军队。[22]
到了战争行为之中,并以一种令人瞠目的踊跃程度成群结队地加入了联
布,当局部性质的紧张与危机不断累积,他们终于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
以至于一同沉沦,亦不愿对南方地区的种植园园主俯首称臣而任人摆
述的一切心知肚明,他们既不想将自身的命运与棉纺织工业捆绑在一起
周知,而其生命也只能用风烛残年来形容。来自波士顿的年轻精英对上
续地遭受着来自政治方面的非议,棉纺织工业苟延残喘的颓势已是众所
织工业的态度绝非一成不变。身处一场漫长无边的经济衰退之中,又持
一线都与棉纺织工业息息相关,但事情的发展最终表明,学生对待棉纺
学生已然改换了阵营。[21]
尽管这些学生早年生活中的一丝一缕乃至一针
年,虽然此时哈佛大学的校方仍对废奴主义持反对意见,但作为主体的
化,而这一次,总算轮到由洛林来经受人们的唏嘘和非难了。[20]
到1860
一场公众冲突中时,在哈佛大学的校园内,人们的态度正变得愈加分
个名叫安东尼·伯恩斯(Anthony Burns)的逃亡奴隶的命运而卷入到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气氛骤然生变。1854年春天,当洛林因为一
支持。[19]
奴隶引渡原籍。至少在1852年时,学生对追缉逃奴这样的做法仍是鼎力
知名的保守人士,而后者正是美国巡回法庭中的执行专员,专司将逃亡
污蔑。他们将教授职位授予爱德华·洛林(Edward G. Loring)这样一位
想观念公之于众,便会对萨姆纳这位杰出而高产的法律学者进行攻讦与
在高校学术圈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权威人士而言,他们若想要将自己的思
言人,只能从学生那里获得无尽的唏嘘嘲讽乃至质疑怒斥。[18]
而对那些
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7]
在内的一批废奴主义代
该校的校园中,包括查尔斯·萨姆纳、贺瑞斯·曼(Horace Mann)以及拉
得最为突出。早些年间,该校堪称孕育保守主义思想的温床,那时,在
进思想。这种转变在哈佛大学这一备受棉花大王喜爱的民间机构中表现
走向崩塌,而他们自身也愈发倾向于接受那些可能会带来激烈冲突的激
35
伴。亚当斯家族作为声名显赫且与废奴主义运动羁绊颇深的政治世家的
出商业领袖”的小查尔斯·亚当斯,则是希金森的校友兼一同长大的伙
与此同时,另一位最终崛起为“主导了波士顿新型工商业秩序的杰
亲身经历了战斗,并因此而多次负伤。
被调配到了马萨诸塞州第一骑兵团中服役。在布尔朗和奥尔迪两地,他
代的洪流。希金森先是在马萨诸塞州第二步兵团中服役了4年,而后又
希金森26岁那年,他与许多哈佛大学前校友一起,满怀激情地投入了时
足其中。最终,直到南北战争正式爆发,他才被激励着采取了行动。在
政治,即便当原先那种局部化的政治冲突逐渐扩大升级时,他也未曾涉
活,且他的花费绝对超出了这些遗产所能够产出的利息。他基本上远离
暂的当下,希金森主要依靠自己从叔叔及祖父那里继承得来的遗产过
此刻,似乎任何受人尊敬的职业都无法进入希金森的法眼。[26]
在这一短
活,选择一份正经的事业,并将自己的热情和毅力投入其中。但是此时
己的父亲一直保持着联络,父亲曾多次恳求他放弃声色犬马般的闲适生
剧院交际,频繁招待那些从自己的家乡波士顿远道而来的访客。他与自
留驻足在奥地利的首府维也纳。他曾试图学习音乐,却总沉迷于在各大
春花费在了环游欧洲的旅行上,而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光景中,他都停
式已然行将就木。在随之而来的整个19世纪50年代,希金森将自己的青
随着蒸汽动力的粉墨登场,风帆时代正在悄然谢幕,这一古老的商业模
能,但总的来说,希金森并不过分热衷于这一古老的商业模式,毕竟伴
日后的职业生涯大有裨益的会计技巧,并初步磨炼出了自己的商业本
答、马尼拉、爪哇乃至澳大利亚等地。[25]
其间,希金森逐渐掌握了对其
期两年的学徒生涯。此时,这一商团的贸易网络最远延伸到了加尔各
(Samuel)和爱德华·奥斯汀(Edward Austin)的手下,开始了一段为
在希金森因病从哈佛大学辍学之后,他在印度码头商团中作为萨缪尔
内心最深处的动机,同样,他也并不清楚自己的奋斗目标究竟为何。[24]
者的说法,年轻的希金森对自己的人生尚不明确,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
在那个商业前景还不甚明朗的时代,按照曾为希金森撰写传记的作
说,希金森家族并不认为自己的延续需要倚仗于奴隶制度的存在。[23]
南方地区结交了许多朋友。”多年之后,希金森曾如此解释道。总的来
结识的人,无论他们是老是少,都对棉纺织工业有着极大的兴趣,并在
地接受废奴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在波士顿,许多能够为我们所观察并
成员,也正是因为如此,相比于他们的亲朋好友,该家族能够更加容易
要身份的同时,他们并非任何棉花产业相关公司的财务主管或是董事会
家族在一定程度上远离棉纺织工业的核心。在保持着自己作为商人的主
36
美国国内的南北对立以外,更会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组织方式产生
击。”[30]
小亚当斯极富先见之明地察觉到,原棉价格的飞涨除了会导致
理想场所,而这无疑将对美国南方垄断原棉供应的现状给予致命一
完工的、长达数百公里的铁路干线,已将广大的领域变成了棉花种植的
屿,都有可能会成为他们的聚焦之地。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印度那已经
法逾越的广袤荒野、遍布南美的高山台地还是点缀在太平洋上的零星岛
找出替代性的原棉产地。无论是印度次大陆的茂密丛林、非洲那看似无
方农业产区长久地执棉纺织工业之牛耳,因此他们必将放眼全球,并寻
地区在原棉种植领域的统治性地位。这些商业引领者绝不会坐视美国南
和身处曼彻斯特的实业家,将很快采取决定性的举措,以颠覆美国南方
治地位已是摇摇欲坠。小亚当斯如此推论道:“那些来自利物浦的商人
当斯所撰写的报刊文章中,他敏锐地做出了如下判断,“棉花王国”的统
他都在《大西洋月刊》的字里行间权衡着天下大事的轻重缓急,在由亚
亚当斯主要通过在报刊上撰写文稿来让自身与世界时事接轨。每一天,事务,与小亚当斯那巨大的野心相比极不相称。[29]
在那个时间点上,小
回奔波,并时常与对方发生争执。可以见得,这种碌碌无为的日常琐碎
开始涉足亚当斯家族的财富管理事务,他为了从租户那里收取租金而来
著名律师事务所中实习工作,并顺利取得了执业资格。与此同时,他也
后,小亚当斯曾将自己训练成一名律师,他在位于波士顿市中心的一家
希金森一样,小亚当斯对自己也没有一套明确的职业规划。在毕业之
轻时便有如幽灵一般萦绕在他心头,且久久不能消逝。更糟糕的是,与
尽管继承了显赫的血统,但那种对于家族衰败的忧虑在小亚当斯年
着新的财富来源,以期据此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
了多达数千美元的额外补贴。可是即便如此,小亚当斯仍然急切地寻找
议员和外交官的传统)的日常开销,还每年为该家族的新一代成员提供
资组合不但充分地支撑了老一辈亚当斯家族(他们承袭了家族作为国会
股票,在这些财产中所占到的比例微不足道。[28]
这种以保守性见长的投
中心或是昆西地区(他们的家乡)的房产,而那些与棉纺织工业相关的
系,[27]
但亚当斯家族从这份婚姻中得到的财产主要是一些位于波士顿市
所积累的财富必然与奴隶贸易、由奴隶所生产出的商品货物脱不开干
足海洋运输保险领域的先驱。尽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由布鲁克斯家族
Brooks)先生的第四个也是最小的一个女儿,后者既是商人也是最早涉
婚姻而袭得。布鲁克斯小姐是彼得·查尔顿·布鲁克斯(Peter Chardon Adams Sr.)与阿比盖尔·布朗·布鲁克斯(Abigail Brown Brooks)小姐的
着距离。该家族的财富,主要是通过老查尔斯·亚当斯(Charles F. 后裔,一向洁身自好,他们平素里和那些与棉纺织工业有关的投资保持
37
这是因为一来他并非为该产业而生,二来他也没能赶上该产业最好的年
质上说,库利奇与棉花产业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牢固,的过程中,绒布帮曾凭借暴力手段干扰并冲击废奴主义集会。然而从本
顿精英所组成的激进组织“绒布帮”中的一员,在美国逐渐走向南北战争
支持者一道,被归入反废奴主义者的阵营。库利奇在当时被看作由波士
收入。一时间,在政治立场方面,库利奇只得与其他那些棉纺织工业的
在“布特棉纺厂”担任财务主管的职位,而这份工作给他带来了稳定的月
的是,当托马斯几近破产之时,他的岳父威廉·阿普尔顿为他提供了
大人物之间建立起的扎实关系,帮助他们获取了急需的商业信贷。幸运
样,他与他的合作伙伴之所以能够免遭灭亡,完全是因为他们与富有的
到来的经济恐慌中,库利奇险些失去自己的一切,正如他自己记述的那
商人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便开始做起了自营贸易。在随后于1857年
并时常感到自己已被波士顿的主流社会排除在外。在作为学徒跟随一名
年返回波士顿进入哈佛大学就读时,他只能说出一口十分蹩脚的英语,人。当托马斯·库利奇最终结束了自己为期10年的欧洲之旅,并于1847
四个儿子,则被他先后送往位于日内瓦和德累斯顿的寄宿学校中长大成
中国广州,并当上了罗素商行的合伙人,而包括托马斯·库利奇在内的
(Thomas Jefferson)的曾外孙。在19世纪30年代,库利奇的父亲曾移居
从其母亲的角度来看,他甚至还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
比肯山的住宅区中出生长大,他是一个古老的新英格兰家族的后裔,而
会主义骑墙派。与自身所处阶级的大多数成员一样,库利奇也是在位于
亚当斯”等人相比,托马斯·杰弗逊·库利奇其人则更像是脚踩两只船的机
与“以保守主义为特点的劳伦斯”和“以前瞻性而见长的希金森与小
英阶层挽回了不少颜面。[31]
参与到革命性历史事件中的机会,他们也由此在公众领域为波士顿的精
与同志情谊的军旅生涯。这场战争赋予了小亚当斯和他的伙伴一个亲身
出来。他脚穿皮靴,花费数月的时间置身于旷野之中,过起了充满豪情
离了毕业后沉闷的职业生涯,还让他得以从原先社会环境的桎梏中解脱
极践行的参与者,而非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这场战争不仅让小亚当斯逃
也随即抱着极大的热情加入到了军事行动当中。在这场战争中,他是积
在小亚当斯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南北战争便轰然打响,而小亚当斯
终结后得以幸存的乐观主义分子”中的一员。
的动态本质,他将自己视为波士顿那些“坚信工业资本主义将在奴隶制
切变化的人士相比,亚当斯无疑更能适应那种深藏在政治经济表象背后
深远的影响。与劳伦斯那样的因深陷棉花经济体系无法自拔,而反对一
38
在1851年被重贬为奴之事而对宪法欢欣鼓舞的、波士顿最为富有且受尊敬的人士,如何广泛地支持逃奴追缉法案的信息,参见:Manisha Sinha,The Slave’s Cause: A History of
Kimball, On the Battlefield of Merit:Harvard Law School, the 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223-235. 有关那些为来自佐治亚州的逃亡奴隶托马斯·锡姆斯
[19]Charles Warren, History of the Harvard Law School and of Early Legal Conditions in America (New York: Lewis Publishing Company, 1908), 2:98;Daniel R. Coquillette and Bruce A. [18]Morison, Three Centuries of Harvard, 1636-1936, 290.
《论自然》。——译者注
[17]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美国思想家、文学家,诗人。爱默生是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美国前总统林肯称他为“美国的孔子”“美国文明之父”。1836年出版处女作
[16]Crouch, “In Search of Union,” 228, 232.
[15]亚伯拉罕·林肯,美国政治家、思想家、演说家,共和党人,美国第16任总统,黑人奴隶制的废除者。——译者注
[14]Johnson, River of Dark Dreams.
[13]Ibid., 200-201.
[12]Ibid., 218.
[11]Ibid., 226, 237, 217.
害。——译者注
[10]约翰·布朗,1859年曾领导美国人民在哈珀斯费里举行武装起义,要求废除奴隶制,并逮捕了一些种植园主,解放了许多奴隶。起义最终遭到镇压,约翰本人则被逮捕杀
[9]Ibid., 169.
[8]Crouch, “in Search of Union,” 104.
[7]Amos A. Lawrence to Amos Lawrence, Amos Lawrence Papers, vol.2, November 12 and December 22, 1836, MHS; O’Connor, Lords of the Loom,47-48.
[6]January 3, 1837 and January 10, 1837, Box 1, vol.2A, Diaries of Amos A.Lawrence, MHS.
[5]Crouch, “In Search of Union,” 53-57.
[4]Ibid., 76-78; Whit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 Hospit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awrence, Life of Amos A. Lawrence, 49-52.
[3]Barry A. Crouch, “In Search of Union: Amos A. Lawrence and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1970), 64.
University Press, 1995), 207-208, 442-445.
[2]Michael F. Holt, The Political Crisis of the 1850s (New York: Wiley, 1978),201; John Ashworth, Slavery, Capitalism, and Politics in the Antebellum Republic (Cambridge: Cambridge
[1]Oliver Wendell Holmes, The Autocrat of the Breakfast-Table (Boston, MA:Phillips, Sampson and Company, 1859), 304; Hall,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198-206.
中扮演关键角色。
的支持,他们有信心更有能力在未来数十年间的美国政治经济转型过程
虐的手段来驱策劳工。由于能够获得来自美国东部地区的巨量金融资源
致;他们求助于最新取得的科学技术突破,同时也时常采取激进甚至暴
们不断地挖掘着自身的商业本能,将自己的组织与管理技巧发挥到了极
配性阶级的衰败的鞭策,他们的行动往往体现出一种高度的紧迫感。他
整合到一起。由于受到了棉花经济体系崩溃的驱驰,以及其自身作为支
体系中的地位。他们长途跋涉、历尽艰险,努力地将财富积累的新载体
败),这些波士顿市民聚集在一起,深刻地反思了自己在整个国家经济
盾。[34]
但最终,为了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尽管如此也无法免于失
原本身为纺织工业制造商的波士顿精英,一直以来都对这一运动充满矛
提高工人对工资待遇的索求,并稀释掉新英格兰地区的政治权力,那些
必然产物。由于“西部大开发”这一进程,必将导致劳动力从本地流出,在这群波士顿专业投资人士的面前,它们也绝非由原有发展模式带来的
的美国西部地区的那些新兴的且有利可图的投资标的,并没有主动闪现
波士顿积攒的巨额储蓄产出了稳定且高额的回报。[33]
事实上,位于广袤
断萎缩、衰落的颓势,他们开拓出了革命性的新路径,并依循此道利用
颖而出的年青一代,在南北战争结束后出人意料地逆转了波士顿财富不
包括希金森、亚当斯以及库利奇在内的诸多从波士顿原有精英阶层中脱
身,并将自己重新定位为南北战争结束后波士顿金融领袖中的一员。[32]
景。这种实用主义性质的关系,让库利奇能够轻易从棉纺织工业中脱Abolition (New He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509。
[20]“The Slave Catcher’s Commissioner Rebuked,” Commonwealth (May 5, 1854);Coquillette and Kimball, On the Battlefield of Meri, 236-241, 265-266.
[21]Louis Menand, The Metaphysical Club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01), 23-32.
[22]Hall,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23]Ibid., 9.
[24]Ibid., 90.
[25]Ibid., 81.
[26]Ibid., 134.
[27]波士顿商人开展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从17世纪便开始了,而在19世纪早期,这种介入仍在以非法的形式继续着,参见:Hugh Thomas, The Slave Trade: The 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1440-1870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7), 259-260, 534; James A. Rawley,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A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81), 341-351。
[28]Edward C. Kirkland, Charles Francis Adams Jr., 1835-1915: The Patrician at Ba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65. Will of C. F. Adams,Proved at Dedham in the
County of Norfolk, on January 5th, 1887, Adams Real Estate Trust, 1871-1887, Adams Office Papers, MHS.
[29]Kirkland, The Patrician at Bay.
[30]Charles F. Adams, “The Reign of King Cotton,” The Atlantic Monthly, April 1861. 有关棉花经济紧随南北战争的全球转型过程,参见:Sven Beckert,“Emancipation and Empire:
Reconstructing the Worldwide Web of Cotton Production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he American HistoricalReview 109, no.5 (December 2004): 1405-1438。
[31]Charles Francis Adams, Charles Francis Adams, 1835-1915: Autobiography(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16).
[32]Thomas Jefferson Coolidge, The Autobiography of T. Jefferson Coolidge, 18311920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23), 1, 10, 13, 18; Ayer, Uses and Abuses in the Management of
Our Manufacturing; Gross, The Course of Industrial Decline.
[33]这些新兴的商业冒险无疑从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针对几条西部铁路进行投资的先驱尝试中吸取了灵感,但对于一座深受棉纺织工业惠及的城市而言,这些尝试都是相形
见绌的。在19世纪50年代以及南北战争刚刚结束的那段时光,西部商业冒险的金融可行性仍然存疑,类似的例子包括希金森在资金匮乏且迅速走向破产的俄亥俄石油公司中的那段
受雇经历,参见:Higginson and Barry, Life and Letters of Henry Lee Higginson, 240-247.有关波士顿于南北战争爆发前在美国西部地区进行的投资的信息,参见:John Lauritz Larson,Bonds of Enterprise: John Murray Forbes and Western Development in America’s Railway 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Arthur M. Johnson and Barry E. Supple,Boston Capitalists and Western Railroads: A Study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Railroad Investment Proc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Thomas C.Cochran, Railroad
Leaders, 1845-189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34]相关案例,参见劳伦斯针对吞并得克萨斯这一事件所发表的评论——“更多的领土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国土已经从大西洋沿岸延伸到了太平洋沿岸,而仅仅
凭借着我们相对稀少的人口数量,统治如此广大的国土几乎成了不可完成的任务。我们的领土已经太大了,而当年罗马帝国就是因此而衰亡的,她攫取得越多,就越是无法守住自
己已有的财产。”Quoted in Crouch, “In Search of Union,” 62.
39
40
有利可图的。[4]
中。在那个时代,尚没有任何以往的经验能够表明,开采这样的矿藏是
在这些深入地下的矿脉里,铜矿石的品位低,且杂乱无章地分布在其
金属铜才有产出利润的可能,这些砾岩带中的铜含量却仅有2%~4%。
之中。依照传统的经验智慧,一座被开采的矿脉至少要富含40%以上的
继显示出了即将耗竭的迹象,[3]
而新发现的铜矿则隐匿在低含量的基岩
19世纪50年代末,在整个半岛上规模最大也是产出最多的三处采矿点相
渺茫的“飞来横财”让人浮想联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投机活动。到了
石品位极高的矿藏才会有利可图。但这种出人意料的、发生的概率相当
560万美元的股息。[2]
由于铜矿开采和运输的成本极高,只有开采那些矿
资者总共向当地的采矿企业投入了1310万美元的资本,却仅仅收回了
上的94家采矿企业中,只有6家能够做到盈利。从1845年到1865年,投
铜,可就算这样,当地的铜矿开采产业距离完美仍然相去甚远,在半岛
上述的这种方法令半岛上的居民每年都可以产出大约6.35万吨的
形成的泥沙中分离出他们想要的金属。[1]
中分离出来,矿工会先用水力粉碎装置将矿石砸碎,再从矿石被砸碎后
会被装入铁桶中,而后依靠人力或是畜力拉升到地表。为了将铜从矿石
一点地开采出来。铜矿石被装进独轮手推车中推入矿道,在那里,它们
矿法的移民,不畏艰险地利用钻头、铁锹乃至炸药将铜矿石从地里一点
寻找着那些能够产出大量铜矿石的矿脉,来自科尼什地区的精通英式采
结,而一种成产业化规模的经营模式则取而代之。各种股份公司拼命地
被轻易开采出来的铜矿采集一空。这种原始的投机热潮很快便走向了终
勘探者的足迹亦很快便遍布森林湖沼,他们沿着地表和山脊将一切能够
了这片土地。此后,政府将这片土地开放给数以百计的勘探者,而这些
府便随即采取行动,从当地的齐佩瓦族(Chippewa)印第安人手中夺取
已经持续了接近20年的时间。在1842年于该地区发现铜矿之后,联邦政
生。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时,沿着苏必利尔湖而展开的铜矿开采活动,那里,他和同伴使铜矿挖掘作为一项资本高度密集的工业产业而得到重
里之遥的、位于密歇根州的基威诺半岛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商业成就。在
在经历了战争和连续两个棉花种植季后,希金森终于在距比肯山千
一炮而红的卡柳梅特-赫克拉铜矿
41
理者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矿山本身。阿加西斯坚持认为矿井应被重新设
由于利用地面设备处理矿石的能力获得了极大提高,这些新来的管
吨的矿石。[7]
分钟可以敲打矿石90次,依照这种方式,它们每天都可以处理重达800
昼夜地敲砸着矿石,砰砰砰的巨响永不停息”。两台笨重的冲压锤,每
的9月份,阿加西斯才正式宣布捣碎机实现了不间断的工作,“它们不分
捣碎站能够粉碎出规格一致的矿块,以供给自动洗矿机使用。直到当年
加西斯与他的员工不得不花费了数月时间试验摸索,才最终让水力冲压
运输作业。[6]
由于矿山中出产的矿石往往在密度和硬度上迥然相异,阿
还是冶炼工厂,都将能够利用从苏必利尔湖中开入的大吨位蒸汽船进行
米的运河,依靠着这条运河,无论是波蒂奇湖畔的矿山码头、储物仓库
力冲压捣碎站被连接在了一起。另一家附属公司则疏浚了一条长约2千
进行的,花费了数百万美元)。通过这条铁路,矿山与坐落在湖边的水
中穿行而过的铁道线路(这一工作是在阿加西斯的领导下由希金森掌管
相应需求,于是他指挥着工人修建了一条长达约8千米、从茂密的树林
头疼的问题,阿加西斯认为铜矿附近的溪流所能提供的水力,无法满足
的诸多瓶颈发起了攻坚作战。其中,冲压捣碎站的水力供给是一个令人
过。在来自波士顿的规模空前的资金的支持下,阿加西斯对开采流程中
单位金属铜的开采、提取成本,但此时,此等壮举还从未被人们实现
取铜,并使之有利可图的唯一方法。尽管这种做法可以在理论上降低每
“以一种超大的规模连续不断地经营运行”,是从低品位的矿石中提
功地让这一产业迈上了崭新的阶梯。[5]
业的运行。他在荒凉的旷野中度过了20个艰难的月份,在此期间,他成
木工程学学位,亚历山大于1867年3月被派遣到密歇根州,负责这项产
Higginson)的哥哥,同时还是一个名声在外的博物学家。由于曾取得土
项目的现场负责人,他是路易斯·阿加西斯的儿子,艾达·希金森(Ida 躬亲,以期亲自重塑整个产业的运营模式。亚历山大·阿加西斯是整个
Shaw)和亚历山大·阿加西斯不仅掌控着这次商业冒险的全局,还事必
络”整合为这一新兴事业的坚实后盾。他的两个姻亲昆西·肖(Quincy A. 金森公司所掌握的资源”和“由波士顿的富有居民所编织成的社会网
佐治亚州的一团乱麻中解脱出来之后不久,希金森便成功地将“由李-希
低品位铜矿,这是一处位于波蒂奇湖区的未经开发的矿体。在将自己从
季开始涉足铜矿开采这一产业,并为此而购置下了一座名叫卡柳梅特的
投资标的的重任,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去破解这一困局。他们从1866年夏
来自波士顿的投资者,肩负着为巨额资金寻找能够产出足够利润的
42
时的7257吨飞升到了1885年时的约23万吨,而这将近占到了同一时期美
国境内品位最低的铜矿石,这一新型运营模式带来的铜产量便从1871年
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仅仅凭借着从世界上最深的矿井中开采出在美国
总的来说,由这些波士顿人设想并最终付诸实践的新型经营模式取
加西斯将劳工的暴动归因为他们在处理员工不满问题时的过度软弱。[11]
工会组织的图谋不轨这件事情上,公司方面保持了持久的警惕心理,阿
涨,而在其他的时间则一律休想。”在对待“劳工骑士团”的蠢蠢欲动和
绝不能被任何人牵着鼻子走,工资只有在我们认为合适的时候才会上
势。[10]
阿加西斯指示监工在工资的问题上面对劳工一步不退让:“我们
前往镇压,军队随即将罢工的带头人拘禁,并帮助矿山的所有者重掌局
战告捷时,管理者紧急从底特律调集了所属美国第一步兵团的4个连队
他简易武器的劳工对峙,而后当警长与他的人马惨遭失败而劳工群体初
的。先是当地的警长带着18名警官与600余名装备着棍棒、石头以及其
1872年,这次罢工主要是由工资的减少和对更短的工作时间的要求引起
许工人联合在一起而采取一致行动。[9]
第一次主要的罢工活动发生在
另一方面,他们既不允许工人挑战自己在社区管理方面的权威,也不允
院和一所学校,并为由不同宗派的信徒所建立的诸多教堂提供支持。而
制度。一方面,他们设立了一家员工补助基金,在社区中建立了一家医
利裔等。在对待工人方面,希金森和他的伙伴采取了一种家长式的权责
区的主体则是那些外来的移民:康沃尔裔、爱尔兰裔、意大利裔、奥地
围绕着矿山而发展起来的社区已达到了约5000人的规模,而构成这一社
命工作着,同时,还有超过500名员工负责地面上的工作。到1875年,名公司员工一年到头都以一种异常规律的方式遵循着10小时轮班制而拼
在深入地下接近2千米,潮湿且充满硫黄气味的矿道中,多达1000
以及铜饼等成品。[8]
后这些粗铜会被运送到冶炼厂中提纯,并被最终制成铜锭、铜条、铜钉
后,在捣碎站中,人们会采用震动的方式把粗铜从沙砾中分离出来,最
重的蒸汽锤和一部波纹铁颚式碎石机把这些坚硬的矿石轧成碎渣。然
些矿桶运送到数百米之外的矿石加工厂中,在那里工人将使用一台6吨
下,这些满载的矿桶被拉升到地面上。最终,人们会利用高架轨道将这
擎的动力就算不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也是美国国内最强大的了)的驱动
重的矿石,而后在一台功率达到1000马力的引擎(在那个时代,这些引
在那里矿石会被倒入既大又重的矿桶内,而每一个矿桶都能够装载数吨
炸药和气钻来分离矿石,接着他们会将矿石运送到矿山的主要竖井中,计以满足更大规模挖掘作业的需求。在地下作业的矿工队开始使用高爆国铜总开采量的90%。[12]
随着这一事业的发展,被重新命名的“卡柳梅
特-赫克拉矿业公司”再也不是原先那家只靠单一矿井盈利的小型企业 ......
融的力量
[美]诺姆·马格尔 著
刘润基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
3
迈诺特的墨西哥中央铁路之行
亨利·迈诺特的死讯以及其作为金融家的前半生
第三章 豪门的西行
波士顿的税收制度之争
遭吞并地区与未遭吞并地区的对比
大兼并运动的兴起与精英阶层的抵制
都市转型与都市政治
第二章 建设自由放任的都市
走出阴霾
库利奇领导下的投资性资本大转移
再接再厉的堪萨斯奇迹
一炮而红的卡柳梅特-赫克拉铜矿
困境之中的抉择
由棉纺织工业的繁荣带来的一荣俱荣与由其衰败带来的一损俱损
棉纺织经济的终结与新时代的开端
“卡顿山”种植园破产
第一章 对危机的剖析
导论:伟大的转型
序言
目录
4
尚未完成的市场一体化进程
第七章 结论:转型与再出发
《特别税务委员会报告》与民粹主义者的反击
小马修斯对都市政治弊端进行分析并提出应对之策
结盟爱尔兰裔选民以及打压统一化公共教育
小马修斯领导下的马萨诸塞州民主党改革
新形势下伊利教授的税改理论
都市财政吃紧背景下来自精英阶层的绝地反击
第六章 变革年代
表象背后的深层动因与制宪会议的最终结果
民粹主义者的进攻与东部代理人的反击
由西部各州的制宪会议而引发的新一轮较力
第五章 美国东部资金与西部民粹
波士顿公园争夺战大结局
精英阶层眼中的“文化等级制度”
技工群体“一切源于劳动”的世界观
精英阶层站不住脚的历史论点
由争端体现出的对立双方世界观的巨大差异
技工与精英阶层的激烈交锋
由技工慈善联合会的请愿引发的争端
第四章 波士顿公园争夺战
波士顿的金融家在美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迈诺特的铁路公司副总裁生涯学会理解复杂的世界
致谢
版权页
5
6
思维亦将被引入其中。今日的地缘政治学者总结出的一条关键法则——
来的)历史学”,这一点在本书中亦无法避免,因此当今的全球化经济
萌芽的这一主题。“所有的历史学都是(站在)当代的(视角上发展出
主义这一话题的同时,还将重点关注商业资本主义最开始是如何在美国
我们在关注以往那些典型著作所着重讨论的美国是如何过渡到工业资本
型期对重塑美国经济体系起到过关键作用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本书将挑战这些影响深远但过于武断的论述,回顾在这一关键的转
提出问题、剖析问题、解释问题这一完整的流程。
造出有关这一时代的刻板形象。毫无疑问,这样的叙述方式并没有完成
分析,它们将其描述为势不可挡,并企图仅用寥寥数笔便在读者心中塑
据。这些叙述使得有关这一进程的定量性描述完全压倒了文本性历史学
如钢铁产量、工厂产出以及新增移民数量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数
我驱动而实现不断发展的层级复杂的大企业,而在教科书中则罗列着诸
电报等科技发明所发挥的革命性力量,商业编年史中充斥着那些凭借自
了。提到这个时代,一般的文献资料往往会循规蹈矩地提及诸如铁路与
起源至关重要,但不幸的是,这一工作在大多数时候都被人们忽略掉
西部地区的快速拓殖的时代,对我们深切了解美国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
的兴起、美国国家制度的加速形成、城市中心的爆发性增长以及对美国
兴趣点的核心所在。难以否认的是,重新回顾那个见证了大型商业公司
业强国的?就美国在整个19世纪的历史进程而言,这个问题无疑是人们
制共和国又是如何在短短不到40年间就成长为一个具有支配性地位的工
美国如此重大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一个以棉花出口而闻名的奴隶
治体制以及意识形态亦受此影响而被彻底地重塑。
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核心主题,而美国国内的社会关系、劳工制度、政
肉类加工以及最为重要的铁路运输等一系列新型工业,快速地成为美国
进无疑是前无古人的。在这一进程中,诸如冶铁、炼钢、矿业、化工、法国以及英国的总和。对于那个时代,美国在工业生产能力上的巨大跃
身一变,崛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其工业产值超过了当时德国、物——棉花的主要原料供应国,然而在20世纪刚刚到来之时,美国却摇
当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之际,美国仅仅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经济作
序言
7
远的地域与边疆并入一个统一的经济实体之中,这样的蓝图远非天衣无
财富和投资的新边界同时也勾画出了社会争论的新边界,将那些遥
济之路。
的老路,而走上了一条崭新的、以美国国内市场为中心的工业型政治经
次运动使美国资本主义的形态脱离了原先那条以大西洋棉花贸易为中心
范围,并将美国西部地区那些刚刚显露头角的企业转变为业界巨擘。这
列商业冒险行为。这一资本的再分配运动极大地拓展了美国农业的覆盖
移,以资本助长了包括铁路运输业、矿业、农业以及畜牧业在内的一系
士顿在内的古老城镇向地处西部地区的那些处于前沿的投资领域不断转
州、怀俄明州以及俄勒冈州那样遥远的目的地。财富从美国东部包括波
投资到诸如密歇根州、堪萨斯州、伊利诺伊州、科罗拉多州、达科他
集他们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棉纺织工业中积累的资本,并把这些资本
资,这将告诉我们那些被称为“波士顿豪门”的富有波士顿精英是如何调
争的结束而从美国东岸的城市中心流向美国广阔的西部地区的资本投
统的国家视角而未被关注。更为关键的是,本书将追踪那些随着南北战
分析,包括城镇、都市、领地以及地区,这些地方性的实体往往由于传
中,我们将对许多发生在那个时代的地方层级上的重要事件进行追踪和
宏观经济学指标或是简简单单的“工业化”一词所详尽描述的。在本书
以肯定的是,这是一段崎岖坎坷且矛盾重重的历程,它绝非可以被任何
迹,而在于探索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版图在19世纪后半叶的转型之路。可
在本书中,我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于追踪美国的国家经济的增长轨
而必须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主题进行探讨。
时,我们亦不能在政治边界的界定这一问题上进行任何想当然的假设,纪横跨整个大陆的国家经济体系是如何形成的”这一充满争议的问题
纷繁复杂的贸易、外交及力量网络之中。同样的,在研究“一个在19世
张,北美原住民史学家则将印第安部落的历史轨迹深深地嵌入到其内部
之中,奴隶史学家追踪着“棉花王国”在美洲大陆上极具侵略性的领土扩
的国家的历史置于更加久远的、通过大西洋与外界互动的整个历史背景
们对于美国19世纪历史的认知:美国建国初期的历史学家便将这个年轻
的。不断更新的、关于政治边界的渗透性及延展性的认识已经改变了我
不断吸收融入世界经济为特色的时代而言,这样的观念也是不合时宜
机,并以大范围资本流动、充满活力的大都市以及美洲大陆的内陆地区
下,这样的观念显然难以适用。同样,对于19世纪后期那样一个充满生
可以当作在其上发生的所有经济行为的承载体,但在当今的全球化体制
在分析问题时,国家往往并非一个合适的单位,尽管在20世纪一个国家
8
写他们的历史,便是本书的主题。
50年代的人能够预料到未来会发生什么,而镀金时代的美国人将如何谱
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不会是命中注定的,几乎没有任何生活在19世纪
的社会团体及社会观点之间的力量并不平衡,其最终产生的结果却无论
力,而要解释这些基础架构的形成则需要从其结果入手。尽管互相竞争
远的影响。只有异常敏捷的手法才能够掩饰那些塑造了基础架构的努
组合在一起,对发展的结果、资源的配置以及财富的分配产生巨大且深
烈斗争。那些创造了市场的政治及法律基础架构可以以多种不同的方式
划,以及他们对在既有政治框架下被默认的规章准则与特权所发起的激
转,而真正导致这些转变最终发生的原因,往往是战略行动者的精心策
现象的发生既非无缝衔接般地接踵而至,也不似时尚潮流那样不可逆
致科学技术的突破或自由市场的建立。事实上,按照革命的逻辑,这些
的争论,向我们展示了即便是大规模的经济转型过程,也并不一定会导
那些围绕着19世纪末期美国国家工业经济的涌现这一现象而爆发出
分化的发展道路。
家行为最终使得美国在各个地方层级上走出了一条更加平均化而非两极
发了那些气势恢宏同时又受到民主制度控制的国家行为,而正是这些国
之上”的都市型工业化社会。这些运动支持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成功地激
力量去创建一个“建立在充分享有包括自由在内的各种权利的劳动阶层
的,因此借由政治的力量便可以重塑经济的形态,他们希望借助民主的
的拥护者却并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眼中,经济形式的转变是由政治驱使
形式的转变是由那些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所导致的,然而这些民粹运动
一种以生产主义为特征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教条指出,经济
域,但尽管如此,在反对愈发集中化的金融力量面前,它们仍然共享了
议事日程绝非整齐划一,它们也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个政党、组织或地
遵从的条款、规则以及所应获得的报酬进行议价。这些民粹主义运动的
论不休时,他们实际是在就自身加入整个国家商业体系的过程中,所应
部地区的定居者围绕着铁路管理、劳工保护以及资源开发这样的问题争
发紧密的城市系统中为自己的家乡争取到最为有利的地位,而当美国西
间的使用等话题展开讨论时,他们的基本出发点是要在一个内部联系愈
趋势的。当城市中的居民围绕着市政预算、城市司法管辖权以及公共空
地区的草根政治运动是如何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去抵制资本集中化这一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揭示那些发生在美国东部城市地区以及西部乡村
关注那些伴随着美国国内市场在不同阶段的发展而激发出的政治争论。
缝,在各种各样的基于区域范围内的讨论中,本书将上下而求索,着重
9
特金森(Edward Atkinson)这位畅所欲言且在利用自由劳力生产棉花方
模的试验,在南北战争尚未结束之时便早已展开。查尔斯向爱德华·阿
Islands),在那里由新英格兰人所领导的以自由劳力替代奴隶的更大规
Morse)则前去拜访了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海岸群岛(the Sea 要9500美元。”而与此同时,另一位合伙人查尔斯·莫尔斯(Charles F. 支持。希金森曾这样向他的父亲提醒道:“钱宁会去拜访您,并向您索
先生被派遣到了波士顿,以期从他们的熟人及家族那里获得坚实的金融
是有备而来的。来自这三人组合之一的钱宁·克拉普(Channing Clapp)
事实证明,为了使自己的道路能够通向最终的成功,这三位合伙人
涌入市场,战后的美国经济终将因此被带上一条繁荣兴盛的发展轨道。
都将一并得到历史的正名,当由此而产出的巨量棉花供给有如潮水一般
兰年轻人的道德情操,还是那些他所坚信的有关市场主义的信仰教条,然不同的道路上发展前行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无论是这位新英格
隶的生产积极性,那么美国的资本主义事业就真的可以在一条与先前截
在,如果物质激励可以代替肉体压迫成功地激发出那些被解放了的前奴
事关重大,如果自由农业方法论相比于奴隶制度的确是更加高级的存
原先由奴隶完成的工作”这一简单问题。[1]
毫无疑问,希金森从事的事业
能够支撑起棉花种植业”这一复杂问题,简化为“自由劳力是否能够胜任
的开始阶段,希金森便相当明智地接受了有关建议,将“自由劳力是否
而一旦这一尝试取得突破,物质财富也必将随之滚滚而来。在这一事业
事业。这无疑是一场发生在社会变革领域与政治经济领域的伟大尝试,建美国棉花种植业”是否具备可行性这一问题,当作了他们为之奋斗的
老兵所组成的团队之中。他们三人结伴同行,并将论证“以自由劳力重
邦军队中光荣退役后,这位出身高贵的波士顿市民便加入了由另外两名
上,一边焦急地探寻着美国资本主义的未来所在。一年前,在亨利从联
1865年9月,亨利·李-希金森一边徒步穿行在佐治亚州的茫茫原野之
“卡顿山”种植园破产
第一章 对危机的剖析
10
至于这些来自波士顿的新老板,尽管他们展示出了一定的善意,但对这
前景远非那样美好。在原先主人的役使下,他们几乎完全拒绝工作,而
然而在那些被解放的奴隶的眼中,这种新型领导机制所能够带来的
到足以购置私有土地的钱。[4]
观收入,还能够帮助这些工人中最勤奋刻苦的那一批人在几年之内积攒
人。希金森希望他们的计划不仅可以为这些工人带来足以维持生计的可
在自己的雇员心中树立起一种有关体力劳动的新观念,并以此来激励工
马、耕犁土地、劈砍干柴并清除杂草。他们寄希望于通过上述种种方式
森的两位助手也加入到了田间劳动者的队伍当中,与工人一起放牧、洗
金森与他的工人一道擦洗地板、粉刷围墙、敲凿铆钉。与此同时,希金
雇工展示劳动背后所蕴藏着的高贵品质。在翻修种植园中的大屋时,希
心的新生活,这三位波士顿人开始使用一种身体力行的方式,向他们的
家畜。为了帮助这群新近获得自由的人更快地适应这种以物质激励为核
在分配给他们的家庭自留地上为自己种植作物,或是饲养鸡或猪等家禽
属可以通过承担种植园中多种多样的工作来取得收入,同时他们还可以
采摘、分类以及加工的棉花重量的多少来获取一份额外的报酬;工人家
的土地面积的大小获得一份基础薪资的同时,他们还可以依照由他们所
为此精心设计了一套契约方案,按照这一方案,在工人按照他们所管理
多困难与挑战中,如何处理好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才是重中之重。希金森
爆发无疑都令这几位来自城市的波士顿人始料未及。而在他们面临的诸
天气状况、异常毒辣的夏季高温以及不合时宜的降雨,这些问题的相继
之路似乎从一开始便历经坎坷。各种各样的棉花病虫灾害、令人郁闷的
尽管这三位年轻人对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充满信心,但他们的创业
60名被解放的奴隶。
几处谷仓。种植园还有专为工人们准备的生活区域,在那里居住着大约
带有一间被美丽的橡树所环绕的宽敞大屋、一台轧棉机、一座磨坊以及
山”(Cottonham)的种植园。这座种植园不仅包括约3万亩的土地,还
下而去,他们最终在位于布赖恩县的森林深处购置了一处名为“卡顿
具备上涨的空间。在制订出这份计划后,他们三人便向着萨凡纳地区南
6000美元[3]
的回报,这一数字本身便已极其诱人,更不要说其在来年还
能够收获14500千克棉花。若真是如此,每个合伙人将能够从中分得
于奴隶,人们过度忽视了肥料的价值),那么他们在第一个季度便至少
商业计划,按照他的预估,只要毫不吝啬地施用肥料(希金森认为相较
至还将手中那充满活力的埃及棉花种子赠予了他。[2]
希金森起草了一份
面拔得头筹的专家进行了咨询,而后者不仅向他传授了丰富的经验,甚
11
渐对一种新的论断深信不疑,若是脱离了持续不断的监视、鞭策、驱驰
为市场激励能够激发劳动热情的理想早已荡然无存。这些波士顿精英逐
们这里得到帮助却丝毫不知感激!”事情闹到了这种地步,原先那种认
取了丰厚的薪水,受到了良好的对待,并获得了悉心的教导,他们从我
一佐治亚创业三人组中,她曾这样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这些黑人领
为了给自己的丈夫提供一种资本主义范式的家庭氛围,她也加入到了这
子艾达是哈佛大学著名博物学家与地质学家路易斯·阿加西斯的女儿,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消沉抑郁的挫败感与歇斯底里的愤怒感。希金森的妻
事情丝毫无差。当初那澎湃的激情与家长式的职责理念早已消磨殆尽,劳资谈判却又重新拉开帷幕,随之而来的一切都与第一个种植季发生的
希金森先前的预期相去甚远。而到了第二个种植季,又一轮令人崩溃的
收成极差又正巧赶上世界棉价的萎靡不振,第一个种植季的产出与
帮互助、同仇敌忾,而这又极大地惹恼了他们的雇主。[7]
礼。当劳工发现就连他们最基本的愿望都遭到了否定时,他们便开始互
望的底线,而为了捍卫这一底线不受侵犯,他们甘愿接受任何风雨的洗
而言无疑是奇异而陌生的,能够长久地居住于自己的小屋当中是他们期
人。”[6]
这种为希金森所抱持的伦理观念,对于那些刚刚获得自由的劳工
那些拒绝工作者的居所,而这些新引进的劳工既可以是白人也可以是黑
工作与挨饿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将从别的地方引入劳工,并用他们挤占
说:“作为在土地上工作的自由劳工,这些获得了解放的前奴隶必须在
园的仓储中获得补给,还将面临遭到驱逐的风险。希金森曾明确地警告
金森赤裸裸地威胁道:如果工人不去挣取薪资,他们不仅将无法从种植
大多数情况下希金森也从未放弃过挥动“市场机制”这一大棒的权利,希
象,一边暗自祈祷能够尽快地获得一批得力的帮手。[5]
尽管如此,在绝
而薪水可以换取食品与衣物”,希金森一边满怀欣喜地观察着上述现
工所喜闻乐见的商品。“这些工人开始逐渐地明白工作可以带来薪水,开始在种植园中售卖诸如印花棉布、法兰绒织物、鞋靴等这些贫穷的劳
三位雇主采取了双重手段,一方面,他们向工人伸出了“胡萝卜”,他们
充塞了那紧随圣诞节而来的种植季。为了赢得工人们的支持与配合,这
为这些波士顿人所支付的薪资严重不足,这直接导致罢工与停工的浪潮
种理想在希金森等人的眼中却无异于痴人说梦。更加要命的是,工人认
英亩地(约240亩)、一匹马”那样的美国梦从未被彻底地放弃过,但这
之中。”事实上,在这些被解放了的前奴隶的心目中,从美国分得“四十
算得上公平。希金森曾这样记述:“他们沉迷于一种将土地平分的执念
由的人曾坚定地认为,只有将这片由他们世代耕作的土地均分给他们才
些前奴隶来说也好不到哪儿去。在这三个人到来之前,这些新近获得自以及系统性的督导,这些获得自由的前奴隶将永远无法可靠地完成工
作。希金森夫人如此坦白道:“这是多么令人失望啊!”[8]
第二个种植季
最终带来了比第一个种植季还要严重的亏损,这也让这几个波士顿人更
加清醒地认识到在当前的情况下从事棉花生产绝非什么有利可图的事
业。在1867年5月底,希金森在收拾了自己的行囊之后打道回府,并在
自己的家乡波士顿,加入了由他的父亲和叔叔开办的、实力雄厚的李-
希金森家族银行,正式地开启了一段即将持续数十年之久的崭新的职业
生涯。
[1]有关发生在“卡顿山”种植园中的实验的描述,参见:Henry Lee Higginson and Bliss Barry, Life and Letters of Henry Lee Higginson (Boston: The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21),247-266; Charles F. Morse, A Sketch of My Life Written for My Children (Cambridge, MA: Privately printed at the Riverside Press, 1927),26-32。这条建议是由希金森的战友弗朗西斯·钱宁·
巴洛将军提供的。有关那个规模庞大,且更为世人所熟知的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岛之上的实验的具体情况,参见:Willie Lee Nichols Rose, Rehearsal for Reconstruction; the Port
Royal Experiment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4); Steven Hahn,A Nation under Our Feet: Black Political Struggles in the Rural South From Slavery to the Great Migration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Eric Foner, Reconstruction: 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1863-1877(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8)。
[2]有关阿特金森是如何提倡这一事业的信息,参见:Edward Atkinson, Cheap Cotton by Free Labor (Boston: A. Williams, 1861)。
[3]根据在DouarTimes网站上的查询,1914年1美元的购买力等同于2018年24.65美元的购买力。——译者注
[4]Higginson and Barry, Life and Letters of Henry Lee Higginson, 254-256.
[5]Ibid., 253,254.
[6]Ibid., 254,252.
[7]Ibid., 264.
[8]Ibid., 262,257, 265.
12
13
荣辱兴衰都已被绑定在了棉纺织工业这条大船上而随之跌宕起伏。棉纺
工,还是那些至关重要的手握城市中富有家族资金储蓄的金融机构,其
域之间的交通动脉、波士顿港口内的商业码头、数以千计的棉纺厂职
建。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新英格兰地区乡间田野上的溪流瀑布、区
铁路、仓储以及那些“连接了生产端、供应端和消费端的港口码头”的修
之中。巨量的金融资源被用于资助修建分布在全美国及全世界范围内的
的土地改良以及与之相关的对工厂建筑、机修工厂以及工人宿舍的修建
计的美元被投入到了围绕着水力磨坊的工厂建设、环绕着新兴工业城镇
工业所产出的丰厚利润则往往又被重新投资于这一行业本身。数以百万
地区修建在溪流旁的水力磨坊进行纺纱纺织”这一事业上,而由棉纺织
中,波士顿的商业领袖们曾将他们的全部财富都押注于“利用新英格兰
样,它也并非一帆风顺或承袭天命的。在南北战争爆发前的半个世纪
贯穿于整个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绝不是简单而线性的,同
新制度”的动因之所在。[1]
资关系以及新式资本主义版图在内的一整套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资本积累
不为人们所注意,但最终“促使棉花经济孕育出包括新兴产业、新型劳
且不可逾越的鸿沟之上架构起了连通的桥梁,并向我们揭示了那个平常
部与西部,整个美国各地区以及都市层级上的发展之间那看似根深蒂固
历史上那充满活力的区际联系。它们在南北战争前后,在美国北部、南
美国的旧城镇中,它们与商业之间有着历久弥新的纠葛羁绊,并凸显出
主义的前行轨迹,也穿插点缀于这段历史之中。这些事迹深深地扎根于
一个重要节点,而类似希金森那样的波士顿人的职业生涯以及美国资本
言,那种尝试在废除奴隶制度后重建棉花种植业的努力,无疑是其中的
极度破碎,且被不同的地域和时间片段划分为无数碎片的漫长历史而
决定性的转折。对于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的那段在人们的意识中
领域开始逐步扩展到政治领域),而美国资本主义的剧目也随之发生了
过程中,来自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北方人逐步退出了(这一撤退从经济
的开端。毫无疑问,繁重的美国南方重建工作正在渐次展开,但在这一
示着美国棉花种植业黄金时代的落幕和一套新型的即将到来的产业秩序
对希金森和他的伙伴而言,发生在卡顿山种植园中的一切似乎正昭
棉纺织经济的终结与新时代的开端织工业逐渐在马萨诸塞及其周边的各州中占据了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它
带来了一种使工业化成为可能的区际联系,而那个在“逐渐走向工业化
的新英格兰地区”与“依靠奴隶从事棉花种植、采摘、轧制的美国农业化
南方地区”之间形成的强大联盟,无疑是这种区际联系的突出代表。[2]
14
图1.1 这是陆军少校亨利·李-希金森身着联邦军制服拍摄的照片,他很快便会成为波士顿最为重
15
冒险之中。
一系列包括矿石开采、畜牧养殖以及铁路建设在内的开天辟地般的创业
们从与棉花相关的领域抽身离去,转而投身于发生在美国西部地区的那
举动当作支撑点,这些波士顿精英开始急剧地拓展自身的商业视野。他
为(尤其是对于那些以刻板和保守而闻名且小有建树的经营者而言)的
化”这一充满雄心壮志的宏图大业。把一系列被当时的人们视作胆大妄
的经济框架进行小修小补,而是瞄向了“在整个大陆范围内推进工业
新构思美国资本主义的未来,这一行为不是为了对那种在早些年间形成
栖身的产业,并以此为出发点走出了一条全新的发展轨迹。他们开始重
展的新途径。就好似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波士顿的市民背离了他们原先
急于打造出资本积累新循环的紧迫感,便催促着人们走上了一条商业发
旗舰产业深陷危机,无法在吸收巨量投资的同时产出足够的利润,那种
前的棉花经济能够重获新生的激情与冲动,亦随之迅速冷却。当原先的
植业新篇章”那样的幻想抛到了九霄云外,那热烈企盼美国南北战争之
开,但包括希金森在内的一群波士顿商业精英,迅速地将“开创棉花种
在美国南方那个曾经的棉花王国的废墟之上,重建工作正在艰难展
可能转变为可能的奴隶制度。
南北战争的结局已经从事实上摧毁掉了那个曾经让大规模棉花种植由不
样,众多的波士顿商业精英仍然幻想着重新点燃棉花经济的火种,哪怕
尝试。正如在前文中提到过的“希金森在佐治亚州进行的大胆冒险”那
波士顿的商业精英义无反顾地不断做出复兴甚至进一步扩张这一产业的
在之前的时代中展现出的那种不断自我激励、自我强化的活力,诱惑着
疑将棉纺织工业继续当作经济增长引擎这一做法的可行性,但棉花产业
失,而整个棉纺织工业也随之经历了一场严峻的危机。尽管人们普遍质
个棉纺织生态。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纺织工厂的盈利能力逐渐流
了商业范畴的广泛根基,也将高度的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能力赋予了整
的发展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为这一进程所倚仗的、延伸范围早已超越
社会的最顶层到最底层)以及整个区域的精神和文化生活都与棉花产业
行政机构、社会组织以及民间机构之中。政府的行为、阶级的分化(从
仅限于经济领域。事实上,这一进程已然深深地扎根于新英格兰地区的
在那个年代,就以棉花为根基的工业化进程而言,其影响范围绝非
(Boston: AtlanticMonthly Press, 1921)
图片来源: Bliss Perry,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Henry Lee Higginson 要的投资银行家这次事关重大的“转向西部”运动影响深远。通过这次转型,波士顿
从原先的区域制造业中心被重塑成了整个美国最为重要的金融中心之
一。在经历了将近十年的停滞之后,这一新兴运动无疑为那些急于寻找
能够产出足够回报的投资标的的资金指明了一条出路,并为那些早已准
备好迎接挑战的波士顿富裕阶层中的年青一代,展示出了一幅宏伟蓝
图。这一运动还极大地增强了波士顿精英对于金融行业的信心,并将一
种全新的使命感赋予那些历史悠久的古老社群。坐落在波士顿州街
(State Street)上的城市商业区,很快便呈现出了一幅熙熙攘攘的繁忙
景象,而在波士顿当地的政治圈中,那种试图探讨“该城应在这一新兴
国家经济实体中扮演何等角色”的争论,也日益甚嚣尘上。而与波士顿
经历的这种种变化同等重要的是,美国那辽阔的西部也开始在来自美国
东部地区的巨额投资的带动下逐渐改头换面。一波又一波闻所未闻、规
模空前的美国东部资本浪潮,以势不可挡之势争先恐后涌入大陆腹地,极大地充实了西部地区的商贸网络。金融家由此获得了对美国原先那种
临时性质的、碎片化的且往往是十分脆弱的产业布局进行重新整合的机
会,而作为这一整合的最终结果,一种在东部城镇中的商业区的统一领
导下,集系统化、稳健化、高度资本聚集化等特征于一身的新型产业布
局应运而生。一系列回报丰厚的新兴产业部门逐渐发展为美国资本主义
的内在核心。最终,依靠一种在政治领域备受争议且在社会领域亦极具
变革性的手段,美国的西部地区及其看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资
源、价值不菲的矿产及农作物一道,被成功地纳入了美国经济的整体大
循环之中。
[1]有关美国南部棉花王国的崛起与北部工业化进程之间的跨越区域的联系,参见:Sven Beckert,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Knopf,2014); Edward E. Baptist,The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 Slaver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Walter Johnson, River of Dark Dreams: Slavery and Empire in the Cotton
Kingdom(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Sven Beckert and Seth Rockman, eds., Slavery’s Capitalism: A New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值得注意的是,奴隶制的消亡与战后美国工业化进程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得到同等级别的关注。
[2]有关这些区际联系的信息,参见:Thomas H. O’Connor, Lords of the Loom,the Cotton Whigs and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 (New York: Scribner, 1968).
16
17
旷神怡的乡村环境之中”,这种工厂运营方式被誉为美国独特的工业化
居住于受到严密监控的宿舍中。“不会永为工薪阶层,且生活在令人心
司操作工厂中的机器,在此期间的若干年中(在她们结婚之前)她们将
劳刻苦的年轻女性构成,她们从新英格兰地区的乡村中被招募至此,专
的20座城市之列。在这座城市中,劳工群体主要是由那些处事干练、勤
州规模第二大的集市城镇,而到1840年,该市更是得以跻身于美国最大
型棉纺织工厂的落成。在这一过程中,原先的乡村田野成长为马萨诸塞
后,发生在这一地区的规模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便带动了多达19处的大
一处落差高达9米的瀑布旁打造一座全新的产业基地。仅仅在不久之
先的创业者在一种更大的野心的驱使下,决定在洛厄尔市梅里马克河中
1822年,受到在沃尔瑟姆市所发生的奇迹般的成功的鼓舞,那些原
原棉被直接加工为成品布料,而这样的创举为人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纺纱到织布的整个棉纺织工业流程都能够在其中完成。在这座工厂中,们创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将上下游完全整合到一起的一体化工厂,从
——的资本投入的资金,作为股本注入到了这一新成立的公司之中。他
章程,而后将十倍于公司的前身——一座位于罗德岛上的小型棉纺厂
瑟姆市的查尔斯河河畔建立起了波士顿制造公司。他们一同制定了公司
和帕特里克·特雷西·杰克逊[4]
的带领下,率先在地处马萨诸塞州的沃尔
格兰地区的商人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团体,在弗朗西斯·卡博特·洛厄尔[3]
上,这一产业在其漫长的生命跨度中往往黯淡无光。1813年,来自新英
极其出彩的开局,往往使人们在对其未来进行预测时产生错觉,事实
疑是对那些棉纺织工业开创者的极佳写照,但由棉纺织工业所展现出的
的发展前景,我们离过度投资还相去甚远。”[2]
这种自信满满的说辞,无
证:“的的确确,大量的资本正被投入这项买卖当中,但面对如此广阔
人实业家内森·阿普尔顿[1]
曾这样向他那满腹狐疑的友人做出了保
夷所思。那时,他们正一股脑地扎进棉花纺织这一产业当中。1821年商
工业而转投于“美国西部大开发”这一事业,还有如天方夜谭一般令人匪
对那些来自波士顿的商人而言,仅仅在数十年前,彻底放弃棉纺织
其衰败带来的一损俱损
由棉纺织工业的繁荣带来的一荣俱荣与由
18
由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和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格党当作自身政治理念的载体,并凭借着该党踔厉风发的领袖集体——
典城”这一梦幻般的标签。最终,这一身为“棉花领主”的核心阶层将辉
士顿这座将自己化身为美国工业革命轴心的伟大城市赢得了“美国的雅
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9]
在内的一批杰出人士,为波
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奥利弗·温德
了足以为那个时代定调的喉舌。包括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家、神学家以及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而把这批人加总在一起,便构成
显赫的民间机构中身居要职。他们资助了一系列杰出的作家、法理学
州总医院、波士顿图书馆、洛厄尔学院以及至关重要的哈佛大学等声名
问,该阶层是整个社会的金主,而这一阶层中的成员亦在包括马萨诸塞
阶层,这一阶层通常聚居在位于比肯山住宅区的典雅寓所之中。毫无疑
时,那些手中握有回报丰厚的股票份额的波士顿人,则结成了一个新的
秀,则跃升为了当地社群乃至整个国家中最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与此同
特·劳伦斯和内森·阿普尔顿那样的成长于乡村而发达于波士顿的后起之
传承悠久的商贸世家,重新树立起了自己的金融及社会形象,而像阿伯
层面、社会层面还是政治层面皆是如此。[8]
如同杰克逊和洛厄尔那样的
群体巩固了自身的地位并牢牢地站稳了脚跟,而这种现象无论是在经济
十家的棉纺厂并雇佣着数以百计的工人。依靠着这样的家底,这一核心
握着多达30家以上的超大型纺织公司,而每一家这样的公司都坐拥着数
里,一个由约80位波士顿市民组成的核心群体便脱颖而出,他们共同掌
这样的产业体系在19世纪40年代达到顶峰。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
分销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7]
着流动资本;而数不胜数的销售代理,则将那产量日益增长的棉纱布匹
变为可能;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为固定资产占比极大的棉纺织工业提供
到位于波士顿的港口;机器制造商组装出各式设备,将大规模纺纱织布
万磅计的原棉运入工厂之中,而后又将出产自这些工厂的成品布料运送
于“波士顿—洛厄尔”“波士顿—伍斯特”那样的区域铁路干线,将数以百
有着紧密的联系)打造出了一套连锁系统。在那个年代,诸多类似
及机器制造在内的各行各业之间(这些行业中的企业普遍与棉纺织工业
广泛存在于企业主阶层之中的凝聚力,他们在包括银行、运输、分销以
多佛以及奇科皮等地在内的整个地区中四处开花的繁荣景象。[6]
依靠着
了棉纺织工业当中,充足的投资造就了棉纺厂在包括曼彻斯特、索科、在随后的20年中,洛厄尔模式的支持者将他们的盈利所得重新投回
模式,向世人不断强调这一模式与美国国家的共和制度相匹配。[5]
19
波士顿最为优秀且明智的精英,他们善于预测,极富科学素养,并精通
划”。[14]
这两座新兴城镇的创立者并不是那些贪得无厌的暴发户,而是
评价的那样,“这是由富有而精明的人们所制定的一项规模宏大的计
作,正如这两个项目的投资者之一威廉·阿普尔顿(WilliamAppleton)
发生在劳伦斯和霍利奥克的一切绝非什么未经深思熟虑的即兴之
方面域追加投入3000万美元到4000万美元资金。[13]
民。而为了充分地利用这两个新近落成的产业基地,人们还将在工厂建
终拥有足以匹敌洛厄尔的庞大人口,并在5年之内入住大约3.3万名居
织机数量将提升大约50%。项目的推行者预计,这两座新兴的城镇将最
装置的水力资源,而当这些纺纱装置最终全部建成时,新英格兰地区的
付出了上述的诸多努力之后,这两个地点获得了足以带动150万个纺纱
拓展了城镇的范围,以容纳更多的教堂、学校、公园以及工人宿舍。在
条宽广的运河,他们同样为该项目建造了最为先进的机器制造工厂,并
便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其中,他们为此修建了一座巨大的堤坝并开凿了一
范围尺度上复制原有成就的努力。早在项目的开始阶段,项目的支持者
目,不但得到了规模空前的庞大资本支持,更代表了人们想要在更大的
为“劳伦斯”,而另一个被命名为“霍利奥克”。发生在这两个地点的项
划,正在两个看似前途光明的地点稳步地推进着,其中一个地点被命名
在那个普遍繁荣的19世纪40年代,企图开启棉花产业发展新阶段的计
近极限,随即棉花产业进入了一种缓慢而线性的扩张阶段。有鉴于此,难。在洛厄尔以及与之相类似的其他地区,人们对水力资源的利用已接
现想要为他们那日益增长的资金池找到合适的投资标的,正变得愈发困
为继的。随着已有的资产不断地产出收益,身处波士顿的投资者渐渐发
然而事与愿违,这一所谓稳固的资本积累策略很快便被证明是难以
运转并持久性地产出稳定红利之上。
(即围绕着棉纺织工业构建起来的商业、社会和政治关系网)可以顺利
赚取钱财。”[12]
毫无疑问,他将自己的期望完全寄托于这一复杂的系统 起来的安全的机器正常运行,我便可以以我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快的速度
来:“对于我来说,只要我的商业智慧足以保障那些由我的叔父所搭建
时,他对自己的前途胸有成竹。阿摩司曾这样向人们解释其信心的由
作为这一宏伟事业的接班人而进行培养,当他于1835年从哈佛大学毕业
漏、万无一失的。年轻的阿摩司·劳伦斯(Amos A. Lawrence)从小便被
入。[11]
在那个时刻,这一紧密编织起来的巨网在世人看来无疑是百无一
议程之中,无论是在州层面还是在联邦层面,他们都有着广泛的介
Webster)[10]
所结成的联盟,成功地将他们的影响力深刻地施加于政务
20
和打击,“绝大多数资产都已被视为毫无价值,而对那些尚有财力物力
个联系紧密的,通常将自己视为谨慎而谦和的投资者群体所造成的困扰
殆尽,而人们的信心则更是如此。”阿摩司尤其注意到,这种恐慌对那
观察到的那样,“现阶段,我们能够从棉纺织工业中赚取的利润已消失
的总市值与原先相比至少蒸发掉了三分之一。[20]
就如阿摩司·劳伦斯所
的企业,其投资价值也早已大不如前。总的概括起来,整个棉纺织工业
整个棉纺织工业中的最大的经销商。就连那些侥幸逃过一劫而免于倒闭
值的40%~60%,共有五家大型公司宣布破产,而其中的两家正是原先
愈发凸显。那些与棉纺织工业相关的股票的市值,大都跌到了其票面价
企业迅速蔓延到整个棉纺织工业时,一直埋藏在这场危机背后的隐患也
掌控着的工业重镇,由此成了历史中的绝响。当倒闭狂潮由最新创办的
为过眼云烟。[19]
这两座规模宏大、经过了精心策划并由波士顿核心团体
克推入了破产清算的深渊,而在这一过程中大约有1000万美元的投资化
于1857年接踵而至的金融恐慌,将早已困顿潦倒的劳伦斯和霍利奥
粉厂、线材厂以及造纸厂一类的规模较小的企业使用。[18]
纺织工厂来此安家落户,便只得以更为低下的费率将土地租赁给诸如面
器所能提供的产能仅得到低效的运用。该项目的业主无法吸引到足够的
在该城镇之中,水力资源的供给远远超过了需求,而那些造价昂贵的机
克计划背后的哈德利福尔斯公司,其糟糕的表现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快便发展到了无法被忽视的地步,而其股价也应声下跌。至于霍利奥
着该公司的股价。[17]
可惜好景不长,这家公司在金融方面所面临的困境
损,但那种弥漫于投资者之间的、对于该项目的坚定信心,坚实地支撑
间,尽管负责建设这一项目的母公司埃塞克斯公司经历着经营上的亏
布机的机械制造工厂,是否真的能够创造价值。[16]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
些为了促进这两座城镇的繁荣兴盛而被建造出来的用于生产纺纱机与织
利润足以让投资者在未来数年之中一无所获。阿普尔顿也同样质疑,那
理位置对于一座工业城镇而言可谓得天独厚,但由产能过剩带来的微薄
泻到了早已饱和的市场当中。阿普尔顿敏锐地察觉到,纵使劳伦斯的地
中的、不可胜数的棉纺工厂全部投入运转时,又有大量的过剩产能被倾
这两座城镇的兴建更是对这一问题火上浇油。当那些坐落在这两座城镇
那个一直存在于棉纺织工业之中的产能过剩问题,而劳伦斯和霍利奥克
免于灾难性的结局。19世纪50年代的早些时候,就连阿普尔顿也看出了
虑后的举动,还是波士顿最富有经验的商人们的督导,都未能让该项目
何对失败的恐惧。[15]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最终无论是那些经过了深谋远
行动是基于最为可靠的商业预测,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他们心中没有任
与重工业及工程施工领域有关的实用知识。这些精英坚信,他们自身的
21
多世纪中,波士顿的商业精英一直坚信,对棉纺厂进行再投资既可以消
这一无解的僵局对于整个区域而言无疑是一个噩耗。在过去的半个
式已丧失了可行的基础,而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
置。[28]
上述建议正式宣告了原先那种推动了地区经济发展的财富积累模
营、巩固现有份额之上,而上马新项目这样的扩张手段则应暂时搁
议这一时期的棉纺织工业制造商应将自身的首要任务放在维持企业运
并对任何企图进一步扩张棉纺织工业的行为表达出明确反对。委员们建
是一种持久性的结构化趋势。该委员会很快便将自己的结论公之于众,们清醒地认识到棉纺织工业的衰退与其说是短暂的偶然现象,倒不如说
乐观态度的人带去了一记重击。在头脑冷静地做出了上述评估之后,人
象,进一步加剧了整个世界市场的饱和态势,并为那些对棉纺织工业持
德国、奥地利、法国以及瑞典等欧陆国家之中的棉纺织工业产能扩张现
有个别公司没能按时分红派息。[27]
雪上加霜的是,同一时期发生在诸如
下降到了1846年的9.7%,而后更是跌至了1859年的5.8%,而在这期间亦
公司的股息率,一直处在衰退之中。这一比率先是从1836年时的11.4%
是做了怎样一件天大的蠢事。”[26]
事实上,那些身处棉纺织行业当中的
数十年中这些公司所摊派的股息红利列出一张清单,就会发现自己究竟
仔细地审视一下这一时期新英格兰地区相关公司的股票价格,并就过去
场对原材料的需求增加,极大地推动了原棉价格的上涨。[25]
“如果我们
上游的原棉生产相对不具弹性,中游纺纱纺织产能迅速扩张而导致的市
格下跌到了所谓的难以赢利的“饥饿点”;而另一方面,由于位于产业链
方面,由于棉纱布匹产能过剩、供大于求,相关产品在下游市场中的价
背景下,那种激进的大规模扩产计划居然还能吸引着人们前去冒险。一
贸易委员会也同样哀叹,纵使在现有工业城镇的棉纺厂产能快速激增的
厂的过度投资”,便是该委员会对这次危机成因的明确论断。[24]
波士顿
创的资产都是由从属于该州的资本所持有的。“对棉纺厂和机械制造工
这次衰退对马萨诸塞州的资本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毕竟,许多遭受重
想。波士顿贸易委员会针对整场危机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并严厉谴责了
棉纺织工业的衰退迫使波士顿的商业精英痛苦地抛弃了原先的幻
居或熟人都已经沦落到了一无所有的境地。[23]
找资金。[22]
阿普尔顿也同样观察到,他的许多曾经自认为十分富有的邻
为艰难的日子里,他每天都在绝望之中为自己那逐渐走向没落的产业寻
陷其中。”[21]
威廉·阿普尔顿也私下承认,在那段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最
这一产业的人们都已沦为乞丐,而不幸的是,许多我最要好的朋友便身
在彼此之间订立合同的人而言,信任感也已经不复存在。许多严重倚赖
22
余的资金流入更加宽广的、以“为棉纺织工业公司与区域性铁路公司的
后,该公司主动缩减了这类贷款的规模,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允许多
然而,这些贷款很快便饱受监管困难以政治争议的困扰,以至于1838年
投入新英格兰地区的乡村田野,并为生活在美国西部的农民发放贷款。
算师便开始为公司寻找替代性的投资出路。他们先是将公司的盈余资金
士顿地区并不能够算得上是十分广阔的市场走向饱和之时,该公司的精
成立于1823年,最初将其资金投入到地产抵押贷款之中,而当这一在波
说,其最主要的存放之地便是“马萨诸塞州医院人寿保险公司”,该公司
线。对于那些最初从波士顿地区海事活动中赚取并积累下来的资金来
与此同时,新英格兰地区的金融机构也遵循了一条相似的战略路
济生态则逐步取而代之。[33]
齐放的经济生态也随之日渐凋敝,而一种以单一和乏味为特色的新型经
关的产业时,那种曾经在新英格兰地区居于主导地位的多姿多彩、百花
额。[32]
当商人逐渐放弃自己原先从事的事业,而投资于与棉纺织工业相
美元的资产,且这些资产在由他所构建出的投资组合中占据了35%的份
19家棉纺织公司以及1家铁路公司中分别持有约合42.8万美元以及12.9万
而转投资到了新英格兰地区的棉纺织经济之中。截止到1851年,库欣在
欣(John Perkins Cushing),也将自己的资本积累从贸易领域中撤出,着30余年在中国广州口岸经营商贸而挣得了巨额财富的约翰·帕金斯·库
家区域性铁路公司中同时身兼股东和董事。[31]
而斯特吉斯的好友,凭借
跟众人一般对棉纺织工业进行了广泛的投资,他至少在6家纺织公司和4
这个从东印度地区的商贸活动中赚取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桶金的商人,也
厄尔、劳伦斯以及索科等地。[30]
威廉·斯特吉斯(William Sturgis)——
的股票以及3家水利公司的股票,而上述的诸多公司则广泛地分布于洛
持股,此外他还购入了2家区域性铁路公司的股票,1家纺织机械制造厂
资领域。到1847年,亨利·李共在多达22家从属于棉纺织工业的公司中
的关税保护机制,但最终也张开双臂拥抱起了棉纺织工业这一新兴的投
贸易商,虽然也曾批判为了扶持本地产业而致使进口商品变得更加昂贵
(Henry Lee)和哈里森·格雷·奥蒂斯(Harrison Gray Otis)那样的资深
投资于区域性铁路公司的行为,也早已成了一种风尚。诸如亨利·李
的波士顿市民而言,那种逐步将自己的资产转移到棉纺织工业当中或是
运输业务从未停息,但即便是对于那些发家、崛起于长途运输行业之中
在更加久远的年代中曾被新英格兰地区的富有阶层当作主营产业的远洋
整个地区的政治经济生态都已牢固地构筑在了上述假设之上。尽管那个
列行为事实上又间接地促进了棉纺织工业的产能扩张)。[29]
久而久之,化掉他们先前赚取的商业利润,又可以从中获取稳定的回报(而这一系
23
(20%)、金融机构(10%)、房地产(13%)以及公用事业(3%)领
资性资产总份额的54%,而在上述的这些资产面前,内森在铁路公司
性地购入这些股票),而这些股票的总估值约83万美元,占据了内森投
总共持有25家棉纺厂及水利公司的股票(内森先生从1813年起开始系统
配置情况中便可窥得一斑。当内森·阿普尔顿于1861年与世长辞时,他
这一点,从诸如亨利·李、斯特吉斯以及库欣等波士顿商业领袖的资产
迅猛崛起导致了其余的工业部门无一例外地失去了大规模资金的青睐,性铁路运输业这一本身便与棉纺织工业水乳交融的行业,棉纺织工业的
种类往往在彼此之间有所不同,但它们无疑同属于一个行业。除了区域
布在不同区域的各式棉纺厂之中,尽管这些棉纺厂所大规模生产的织物
阶层而言,“多样化投资”这一概念往往只意味着将自己的资金投入到分
万名工人,且大部分工人都是女性。[36]
而对于波士顿商业社群中的上流
在新英格兰地区,棉纺织工业成了当地最大的雇主,总共雇佣着多达8
新英格兰地区的棉纺织工业相关资产仍然保有接近7000万美元的估值。
整个产业的危机已经导致该产业的整体市值下降到原先的三分之二,但
共拥有520万台纺纱机以及12.6万台织布机。到了1860年,即便蔓延于
六个州总共拥有380万台纺纱机以及9.3万台织布机,而同一时期美国总
的产值。位于新英格兰地区的六个州主导了棉花纺织这一工业部门,这
四面八方的资本仍在向该产业汇集,且该产业也年复一年地创造出最大
时间节点上,棉纺织工业已经成长为整个美国规模最大的产业,而来自
纺织工业中,该产业的资本聚集程度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那个
到了19世纪50年代末,由于来自波士顿的资本常年稳定地流入到棉
中。[35]
的资金被投放到了那些在马萨诸塞州内部从事经营活动的铁路干线当
公司的总资金池中亦占到了将近一半的份额。同时,还有大约60万美元
美元激增到了接近400万美元,而这些资金在马萨诸塞州医院人寿保险
业相关公司或该行业中的突出人物出面而进行的直接借贷总额,从30万
年到1855年这十年间,以棉纺织工业公司股票为抵押物的,由棉纺织工
司倾向于提供巨额贷款,且其偿还期限通常保持在数年以上。[34]
从1845
(往往期限只有几个月)的商业银行不同,马萨诸塞州医院人寿保险公
织工业一家独大的借款来源。与那些只以适当的资金规模提供短期贷款 路。依靠着上述的经营策略,这家保险公司成功地跃升为了本地区棉纺
圈的核心群体当中开拓出一条十分广阔且还在不断拓宽之中的资金出
进行极为细致的例行甄别的枯燥日常工作之中解脱出来,并在波士顿商
协商安排下,该公司得以将自身从那种负担繁重且需要对各贷款需求方
融资活动进行服务”为宗旨的借贷市场之中。在一种被视为互利互惠的
24
大的纺织工厂的董事会成员名单相互重叠,这些工厂的主要股东几乎全
出了象征权势的堡垒。波士顿图书馆的会员组成与新英格兰地区规模最
赠,[43]
而通过私人领域的资金捐赠,波士顿精英阶层也逐渐为自己构建
育机构之中,这些机构的运转往往有赖于来自波士顿富有市民的捐
类似的集中化倾向同样渗透到了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主要慈善及教
将在棉纺织工业这条大船上风雨同舟。
组合,那么这些从属于不断扩大着的名门望族的成员,便早已命中注定
朋好友。[42]
如果不去考虑这些人各自的专职工作以及他们个性化的投资
导着年度股东大会,同时他们也往往将公司中的重要职位留给自己的亲
阿伯特家族(Abbott)6人。[41]
这些家族利用代理投票的方式持续地主
(Appleton)10人,李家族(Lee)7人,洛厄尔家族(Lowell)7人以及
该公司的初始创办者紧密相连的九大显赫家族,其中共有阿普尔顿家族 克公司于1846年公布的账簿中提及的100个人名中,共有43人从属于与
清楚地向人们展示出,大量的股票是被一群亲族所持有着的。在梅里马
成员之间。在这些公司兼并重组的数十年后,这些公司的股东份额清单
近乎清一色来自新英格兰地区。[40]
事实上,大多数股权转让发生在家族
分之三以上的权益份额大致可以归于约750位股东的名下,而这些股东
究还是有所限定的群体之中。[39]
直到1859年,最大的11家棉纺厂超过四
家、律师、医生以及上述这些人士的女性继承人所组成的规模庞大但终
者不再仅限于其初始发起人,其股东团体便扩散到了一个由商人、实业
人共同开创的企业已拥有了多达400余名股东。当一家公司的股票持有
及。在位于洛厄尔的梅里马克公司成立两年之后,这家由12位初始发起
行股票交易,同时这些股票高昂的票面价值往往也令普通阶层难以企
来源于当地(波士顿地区)。那些富有的股权持有者很少在公开市场进
散至广阔市场之中的匿名投资者之间,同时其所吸取的资本也几乎全部
在那个时代已相当普遍。当然,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权益交割行为尚未扩
在其所有权交割易手的同时保持正常的经营运转,且股权交易这种现象
人物的专利。众所周知,公司制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便是,公司可以
随着时间的推移,持有棉纺厂股票份额这一举动已不再只是那些大
们对其他的产业部门却近乎置若罔闻。
富有的波士顿市民将自己最大的筹码押注在了棉纺织工业上的同时,他
被投资于个人借贷(21%)以及房地产持有(11%)等领域。[38]
在这些
厂,这些资产加总起来占到了他投资组合总份额的67%,其余的部分则
就更加偏重于棉纺织工业了。在1857年时,阿摩司总共投资了17家棉纺
域的投资都显得相形见绌。[37]
至于阿摩司·劳伦斯先生,他的资产组合
25
个地区的广大民众产生深远的影响。
必将急转直下,而这亦将对城市精英、由这些精英所创立的机构以及整
样的背景下,一旦发生在棉纺织工业中的利润萎缩成为现实,经济状况
见的现实便是人们无法找到能够代替棉纺织工业的新型投资标的。在这
取得与棉纺织工业同等规模的经济成果本就十分困难。总之一个显而易
商业精英太多的财力与精力,抑或是因为在其他工业部门中投入技术并
制。[50]
这也许是因为棉纺织工业在数十年中过度迅猛的发展挤占了城市
尔瑟姆—洛厄尔模式”,尚无法在其他制造业领域中被人们成功复
个以“凭借资本高度聚集的工业企业赚取稳定的收益”为核心主题的“沃
在整个运转机制当中,一个贯穿始终却又悬而未决的问题便是,那
社群无法媲美的。[49]
长了波士顿资本家社群的成长壮大,并且其内部强大的凝聚力也是其他
新来者同化到原有群体当中的能力。这样的金融及组织基础,极大地助
展,[48]
这样的现实赋予了精英阶层相同的价值理念,并让他们获得了将
波士顿的商业精英以及那些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民间组织的生存与发
过程,而如今来自棉纺织工业那高度稳定性的涓涓之流坚实地支撑起了
存就如同在风高浪急的海面上行船一般,是一种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
皆捆绑于该产业盈利产出的社会阶层。在久远的过去,财富的积累与留
业已经达到了自身的饱和点时,波士顿早已诞生了一个自身生计与地位
这一切的一切都意味着,当1857年波士顿贸易委员会宣布棉纺织工
济的依赖程度也变得愈发严重。
育、慈善以及社会改良中心的同时,它们对新英格兰地区的棉花纺织经
全地产生收入。[47]
在这些受赠机构依靠着捐款渐渐成长为整个地区的教
快速增加)——被受赠者当成了自有资产一样妥善管理以稳定且十分安
哈佛大学的64万美元(以上捐赠金额仅为1840年记载的数字,其后仍在
波士顿图书馆的15.2万美元、赠予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20万美元、赠予
为建设精英化社会的关键媒介。[46]
这些规模庞大的永久性捐赠——赠予
图书馆及教堂。这些资金改变了学校施教的原有路线,并使该大学转变
了被用来资助学校内法学及神学领域的教职员工,还被用来在校内建造
赠,导致商业利益能够对学校的管理方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私人捐款除
与州政府之间的关系亦渐行渐远。大量涌入的来自波士顿富有市民的捐
会的资助与管控,然而随着19世纪上半叶私人捐赠之风的愈演愈烈,其
佛大学,其原本是作为一所州立大学而被建立,理应受到马萨诸塞州议
该图书馆当时为全美资金最为充裕的非公众图书馆的名声。[44][45]
至于哈
部是波士顿图书馆这一高级俱乐部的会员或捐赠者,而这也最终造就了
26
喜爱,却逐渐地沦为了阶级统治与反动政治的象征。[57]
针对那些“家财
着那种弥漫于哈佛校园之中的贵族做派,这所大学虽然受到精英的由衷
限,甚至身心残缺)之间的、愈发难以逾越的鸿沟,他们还尽情地嘲弄
撮特权阶层与数量庞大的劳苦大众(这些人往往出身低微、教育程度有
背后深深埋藏着的阴暗现实。除了提醒人们特别留意那条横亘在那一小
对立面上,他们毫不留情地向人们揭示出了在这场社会斗争与阶级冲突
(Theodore Parker)[56]
在内的批评家,则旗帜鲜明地站在了辉格党人的
逊(Henry Wilson)[55]
以及这些人中文笔最为犀利的西奥多·帕克 代化社会。而在这场危机的大背景下,包括查尔斯·萨姆纳、亨利·威尔
现社会中所有族群团体的和谐互助为目的、被有效地组织并管理着的现
辉格党人一直在极力鼓吹要建立一种由德才兼备的精英所领导的、以实
作为“工业资本家阶层政治观念载体”的政治势力失去信心。多年以来,秉持家长作风的辉格党人昔日里的旦旦誓言,选民也日益对辉格党这一
波士顿这种江河日下的消极情势,无情地揭穿了那些道貌岸然而又
种使人们逐渐无产阶级化的工业化弊病。
如今再也无法令人们欢欣鼓舞,同时,它还必将无可避免地患上欧洲那
市镇——“一群固化的薪资阶层的窝棚”。那种曾经独树一帜的商业模式
棉纺厂早已褪去了曾经萦绕着其自身的田园气息,堕落为拥挤而肮脏的
的劳工比例不断下降,越来越多的人只得蜗居在狭小的出租屋之中。[54]
尔,就连工人的居住标准也在持续恶化。居住于公司自有的员工宿舍中
的管理者对他们先前曾做出的“为劳工提供良好生活环境”的承诺出尔反
到1850年时的38.6%,而后更是上涨到了1860年时的61.8%。[53]
由于工厂
座典型的棉纺厂中,外来工人所占到的比例先是从1836年时的3.7%激增
之的是一个更加脆弱的移民人群,其中有男人、女人甚至是儿童。在一
年间作为临时劳动力的、出生于本土的女工逐渐在工厂中消失,取而代
的薪水也变得时有时无。[52]
工人的构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些
常态,工人也不再坚守自己的岗位,甚至就连股息的分配与企业管理者
维持工人生计的地步”。随着为了遏制产能过剩现象而展开的停工成为
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劳动力成本被不断挤压,以至于到了一种仅够
同时,工资却停滞不前。工人经历了一波汹涌的失业浪潮。[51]
正如一些
加了至少1倍,而织工也被迫在数倍于原先的织机间往来穿梭。可与此
恶化的生产环境中大负荷地工作——每个工人需要负责的纺纱机数量增
的利润率促使工厂管理者加大了生产环节的强度,导致工人只得在不断
机和政治危机。此时,棉纺织工业早已脱离了其原先的起飞阶段。微薄
了十余年之久的经济萎靡,迅速地发展成了一场影响更加广泛的社会危
为这场灾难火上浇油的是,这场爆发于19世纪50年代的、足足酝酿
27
[6]Ware, 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 142. 这种棉纺织工业内部的连锁反应在相关著作中得到了详细描述: Shlakman, Economic History of a Factory Town, 39-42, 243-
College Studies in History, vol. 20, 1935)。
Profits and Investment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Vera Shlakman, Economic History of a Factory Town; a Study of Chicopee, Massachusetts (Northhampton, MA: Smith Industrial Beginning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31); Spalding, “Promotion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New England”; Paul F. McGouldrick, New England Textil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Origin of Lowell (Lowell, MA: B.H.Penhallow, 1858)。有关这一产业的开端的最为细致的研究,参见:Caroline F. Ware, The 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 A Study in [5]罗伯特·达尔泽尔的记述大致上接受这种乐观的看法,而这与那些创业者在相关著作中表达的自身观点是相一致的,参见:Nathan Appleton,Introduction of the Power Loom, [4]帕特里克·特雷西·杰克逊,美国棉纺织工业先驱。——译者注
[3]弗朗西斯·卡博特·洛厄尔,美国棉纺织工业先驱,完善了现代工厂制度。——译者注
[2]Robert F. Dalzell, Enterprising Elite: The Boston Associate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49.
[1]内森·阿普尔顿,马萨诸塞州纺织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译者注
战争的全面爆发。
运动成功地将妥协这一选项从政治议程中完全移除,并进而促成了南北
敌视态度这两点上,这些运动的参与者却堪称志同道合。[63]
最终,这些
不妥协,以及将那些棉纺织工业巨头视为社会秩序的公敌,并对其采取
地。尽管爆发这些运动的政治诉求与选区千差万别,但在对蓄奴制度毫
动,并最终导致了辉格党在与共和党进行的选战中,接二连三地一败涂
终激发出了包括“自由土地(Free Soil)”[62]
在内的一系列政治反抗运
一个由‘皮鞭之主’与‘织机之主’所结成的邪恶联盟。”[61]
这些口诛笔伐最
贩子,与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厂厂主兼无良奸商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
名的谴责性论断:“路易斯安那州与密西西比州的棉花种植园园主兼人
更是将奴隶问题与精英特权问题放在一起进行思考,并由此而发表了著
这场论战将废奴主义从原先的那种小众议题升级为阶级对立。[60]
萨姆纳
塞州的行政官员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挺身而出,以维护“法律与秩序”。
的棉纺织工业资本家坚定地站在了自己的伙伴身边,他们不断对马萨诸
此而此起彼伏。为了向自己在南方“棉花王国”中的盟友表明忠心,北方
间的裂痕更是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波士顿街头,一系列暴动因
他们原先主人那里”的《逃奴追缉法案》获得通过时,民众与资本家之
视作蓄奴制度的帮凶。而当规定了“应当强制将那些逃亡的奴隶送回到
地。这些北方工业资本家很快便被人们冠以“棉花辉格党”的蔑称,并被
在美国南方的原棉供应者之间的庞大同盟,正逐渐让商业精英名誉扫
萨诸塞州的民众当中深入人心,那个存在于这些北方工业资本家与他们
尽管他们也曾努力抵制这一制度,但从未成功。随着废奴主义逐渐在马
挥之不去的漫漫阴霾。蓄奴制度俨然成了工业资本家最大的政治软肋,此时,围绕着种植园蓄奴制的争论,已悄然发展成了这场危机之中
带来危害。[59]
告道:不断聚集的财富将会给一个工业化的马萨诸塞州原本享有的自由
问。[58]
在对统治阶级以及富人联盟进行口诛笔伐的同时,他们也不忘警
一事实,这些批评家不畏权势,以一种舍我其谁的姿态发出了自己的质
于一切之上的行事方式,以及他们意图为所欲为地操纵摆弄公共机构这
万贯的商业精英”伙同他们“在政治领域内的爪牙”将自身的金融利益置
28
[35]有关马萨诸塞州医院人寿保险公司曾倾尽所能地为马萨诸塞州的农民手上的资金寻找出路的信息,参见:Tamara Plakins Thornton, “ ‘A Great Machine’ or a ‘Beast of Prey’:
Life Insurance Company。
30. 19世纪50年代末发生的大规模亏损并没有见于公司的官方分类账目之中,这一定是由于当时采取了极为激进的会计处理方法,参见:Whit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 Hospital [34]Lance E. Davis, “The New England Textile Mills and the Capital Markets: A Study of Industrial Borrowing 1840-186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 no.1 (March 1960): 1- [33]Moriso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 276.
Larsen, “A China Trader Turns Investor,”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2, no.3 (1934): 345-358。
棉纺织工业的个人或企业。参见:“Schedule of Property,” January 1, 1851, John Perkins Cushing Business Records, Vol.6, Baker Library Historical Collection,Harvard University; Henrietta 大量地产、在波士顿市中心的土地、持有的银行及保险公司中的股票份额、在纽约州北部及宾夕法尼亚州的铁路、政府债券、现钞以及私人借贷,其中的不少借贷都提供给了从事
[32]尽管库欣每年要花费大约5万美元,可谓耗费糜大,但这些投资使他的财富在1831年他从中国返回到1862年他去世时上涨了3倍。其他几处大额资产包括库欣在沃特敦的
[31]Gerald Taylor White, A History of the Massachusetts Hospit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7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123124。
[30]参见:Versa Shlakman, Economic History of a Factory Town, 30; Knneth Wiggins Porter, The Jacksons and the Lees; Two Generations of Massachusetts Merchants, 1765-1844
Merchant and Entrepreneur, 1779-1861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5), 60-61, 110-111, 113。
University Press, 2010),265-267。在内森·阿普尔顿进入国内制造业领域之前,他所从事的事业便是贩卖广东的丝绸和孟加拉的棉花,参见:Frances W. Gregory, Nathan Appleton, 姆斯·劳埃德以及帕特里克·特雷西·杰克逊,参见:James R. Fichter, So Great a Proffit: How the East Indies Trade Transforme Anglo-American Capita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Maritim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 1783-1860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21), 214-215, 225。一些沃尔瑟姆和洛厄尔的初始发起人便是起家于东印度贸易的,包括以色列·桑代克、詹
顿是其位于美洲大陆上的主要目的地,同时波士顿还保持了在整个美国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港口的地位,超过了费城、巴尔的摩以及新奥尔良。参见:Samuel Eliot Morison, The [29]尽管迈向工业化的转型在总体上来说是决绝且只进不退的,但新英格兰人古老的远距离商贸事业从未终止。对于来自东印度群岛、波罗的海及地中海的货物而言,波士
参见:Appleton,Introduction of the Power Loom, and Origin of Lowell.
Press, 1858)。当然,所有人都同意这种低迷将会是长期现象,同时整个体系的结构急需改革。内森·阿普尔顿撰写了辩解书,咬定这次衰落是由小规模生产者的过度竞争引起的,样也有一些详尽描述舞弊与渎职的案例,参见:Report of the Investigating Committee to the Stockholders of the Bay State Mills at Their Meeting, February 5, 1858 (Boston:J. H. Eastburn’s 中化之害,导致了管理上的疏失。参见:James C.Ayer, Some of the Uses and Abuses in the Management of Our Manufacturing Corporations (Lowell, MA: C. M. Langley Co., 1863)。同
话与这场危机的根源相关,比奇洛认为现在的困境证明了公司这种形式与制造业并不相称,而另一位畅所欲言的评论家詹姆斯·艾尔则提出,整个产业遭受到了裙带关系及过度集
Remarks on the Depressed Condition of Manufactures in Massachusetts: With Suggestions as to Its Cause and Its Remedy (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 1858), 23, 17。有一段十分生动的对
[28]Boston Board of Trade, Annual Report, 1858, 54. 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结论。有关资本家不愿继续投资,同时积极地回避整个制造业的情况,参见:Erastus B. Bigelow,分红了。”参见:Joseph G. Martin, Twenty-one Years in the Boston Stock Market, Or, Fluctua-tions Therein: From January 1, 1835 to January 1, 1856 (Boston: Redding and Co., 1856), 42。
多,而多数股东继续持有这类股票的力度仍很强大,这类股票继续贬值的趋势无疑得到了缓和。尤其是考虑到许多这类股票早已不是错过了一到两次的分红,而是连续错过了六次
——“我们所听到的有关这类股票遭遇巨大损失的消息还算不上多,尽管许多这类面值为1美元的股票售价已经跌破了75美分甚至50美分,但由于被真正投入到市场中的股票并不
造类股票的衰落在19世纪50年代的波士顿是众所周知的。而波士顿股票市场的编年史记述者也同样注意到,由于大量股票的交易很不活跃,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遭到了掩盖
势,其资本回报率的平均水平在1830—1834年为10.3%;1835—1839年为9.4%;1840—1844年为6.8%;1845—1849年为12%;1850—1854年为6.1%;而在1855—1859年则为6%。制
32, no.2 (June 1958): 209。大卫检验的九家公司(Amoskeag,Dwight, Cabot, Perkins, Hamilton, Lancaster, Lawrence, Lyman, and Massachusetts)全都显示出了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的态
[27]参见:Ware, 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 113, 151, 153; Lance Edwin Davis, “Stock Ownership in the Early New England Textile Industry,”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26]Boston Board of Trade, Annual Report, 1858, 53-54.
[25]Boston Board of Trade, Annual Report, 1859, 165.
Boston Board of Trade, Annual Report (Boston:Press of George C. Rand and Avery, 1858), 53。
[24]Boston Board of Trade, Annual Report (Boston: Press of George C. Rand and Avery, 1859), 165. 中等级棉花的价格从1843年时的6.25美分上涨到了1857年时的16美分,参见:
Amos A.Lawrence Papers, Box 11, September 1857, MHS.
他还记述道:“可敬的阿伯特·劳伦斯先生损失了大概100万美元,而阿摩司·劳伦斯先生的投资组合则下跌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市值,从45.3万美元缩水到了约29.4万美元。”参见:
[23]尽管相比于自己的邻居,威廉·阿普尔顿的损失并没有那样惨重,但按照他本人的估算,他所持有的制造业股票的总市值从大约60万美元下跌到了大约40万美元。此外,[22]Entries on September 25 and October 1, 1857, in Appleton, Selections from the Diaries of William Appleton.
[21]A. A. Lawrence, Letterbook, October 19, 1857,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MHS).
1859), 163。有关经济萧条的信息,参见:Spalding,“Promotion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New England,” 210。
[20]“股份制公司的股价从没有那么低过,而制造业资产似乎已不具任何价值。”——参见:Boston Board of Trade, Annual Report (Boston: Press of George C. Rand and Avery,1987)。
[19]想要更广泛地了解有关1857年金融恐慌的信息,参见:James L. Huston,The Panic of 1857 and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8]Cole, Immigrant City; Green, Holyoke, Massachusetts.
们不再制造麻烦,参见:Spalding, “Promotion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New England,” 195, 197-198, 209-210。
[17]据说,在一场极为热烈的股东大会上,阿伯特·劳伦斯曾发表了一个小时的长篇大论(也许是不想让他人讲话),并使用极为高超的技巧平息了股权持有者的激愤,令他
[16]December 1, 1885, in Appleton, Selections from the Diaries of William Appleton, 180.
199。
艾德蒙德·德怀特、詹姆斯·米尔斯、萨缪尔·埃利奥特、帕特里克·特雷西·杰克逊、托马斯·帕金斯以及乔治·莱曼,参见:Spalding,“Promotion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New England,” 帕金斯以及萨缪尔·劳伦斯,参见:Hamilton Andrews Hill, Memoir of Abbott Lawrence (Cambridge, MA:Privately Printed at John Wilson and Son, 1883), 24-25。霍利奥克的投资者包括
[15]这些投资者中包含波士顿顶级的商业精英,包括约翰·阿莫里·洛厄尔、威廉·斯特吉斯、内森·阿普尔顿、乔治·莱曼、帕特里克·特雷西·杰克逊、詹姆斯·劳伦斯、托马斯·
[14]William Appleton, Selections from the Diaries of William Appleton, 1786-1862,ed. Susan Mason Lawrence Loring (Boston: Merrymount Press, 1922).
England,” 180-184, 199-209.
[13]Donald B. Cole, Immigrant City: Lawrence, Massachusetts, 1845-1921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3); Spalding, “Promotion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New
[12]William Lawrence, Life of Amos A. Lawrence: With Extracts from His Diaryand Corresponden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888).
Establishment: Upper Strata in Boston, New York, Charleston, Chicago, and Los Angeles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2).
1982); Ronald Story, The Forging of an Aristocracy:Harvard the Boston Upper Class, 1800-1870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0); Frederic Cople Jaher, The Urban [11]Peter Dobkin Hall,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1700-1900: Private Institutions, Elites,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National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任美国参议员。——译者注
[10]爱德华·埃弗里特,美国政治家,曾任马萨诸塞州州长、哈佛大学校长和美国国务卿;韦伯斯特,美国著名的政治家、法学家和律师,曾三次担任美国国务卿,并长期担
国著名法学家,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译者注。
[9]约瑟夫·斯托里,1811—1845年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朗费罗,翻译家,被全世界视为美国最伟大的诗人;霍尔姆斯,美国诗人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之子,他是美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1992), 221; Robert Brooke Zevin, “The Growth of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after 1815,” in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ed.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New Atlantic Slave Trade: Effects on Economies, Societies and Peoples in Africa, the Americas, and Europe, ed. Joseph E. Inikori and Stanley L. Engerma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8]Dalzell, Enterprising Elite, 79, 233-238; Ronald Bailey, “The Slave(ry) Trad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New England,” in The
[7]大约三分之一的成品被运往了美国南部,而另外的10%被出口到了巴西、智利乃至中国等地(出口量逐渐增加),参见:Ware, 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
247; Spalding, “Promotion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New England,” 87-88, 102, 107, 126, 127, 139。A Boston Corporation and Its Rural Debtors in an Age of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27, no.4(2007): 567-597。不出所料,棉纺织工业中的领导人物在随后的
几年中取得了公司的控制权。弗朗西斯·洛厄尔,作为波士顿制造公司创始人之子,成了马萨诸塞州医院人寿保险公司的精算师。阿摩司·劳伦斯、阿伯特·劳伦斯以及内森·阿普尔
顿则成了公司财务委员会的成员。仅仅是靠着极为激进的会计处理方式,该公司的名誉才得以在1857年危机爆发之后继续保持,参见:“Appendix to Actuary Report,” December 28,1857,AA-1 Case 1, 1823-1956, in Massachusetts Hospital Life Insurance Co., Baker Library Historical Collec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36]大约有3万名男性和5.15万名女性,参见:Manufactur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860, ix-x, lxxiii。
[37]Gregory, Nathan Appleton, Merchant and Entrepreneur, 197-198, 271.
[38]Amos A. Lawrence Papers, Box 11, September 1857, MHS.
[39]截至1842年,精确的数字是总共有390名不同的持有者。超过90%的绝大部分的股票都是由商人、地产信托、律师、工厂主、医生、文学机构、妇女(一般而言是前几类
人士的遗孀或女儿)以及那些从商界退休的人士所持有。农民及普通职员拥有的股票不超过总份额的7%,参见:Ware,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到了1859年时,整个
产业的股票中大约四分之一的份额是由女性继承人及地产信托持有的,参见:Davis,“Stock Ownership in the Early New England Textile Industry,” 216,218。
[40]在这段时期,波士顿的总人口达到了接近18万,参见:Ware, 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 Davis, “Stock Ownership in the Early New England Textile Industry”;
Zevin, “The Growth of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after 1815,” 294-295。
[41]Ware, 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 149-150.
[42]Ayer, Uses and Abuses in the Management of Our Manufacturing, 4.
[43]Hall,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72, 110.
[44]1852年波士顿市政议会通过立法使其成为公众图书馆。——译者注
[45]Dalzell, Enterprising Elite, 124-125; Ronald Story, “Class and Culture in Boston: The Athenaeum, 1807-1860,” American Quarterly 27, no.2 (May 1,1975): 178-199. 刨除掉房地产及
大量的文献及美术收藏,它所捐赠的“生产性资产”价值便高达15.2万美元。
[46]Story, The Forging of an Aristocracy.
[47]Dalzell, Enterprising Elite, 159-160. Seymour Edwin Harris, Economics of Harvard, Economics Handbook Serie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0), 368.
[48]我个人对于商业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本质上的不同理解来自皮埃尔·瑞尔威针对这一主题的权威著作,参见:Pierre Gervais, “A Merchant or a French Atlantic?
Eighteenth-Century Account Books as Narratives of a Transnational Merchant Political Economy,” French History 25, no.1 (March 1,2011): 28-47; Pierre Gervais, Yannick Lemarchand, and
Dominique Margairaz,eds., Merchants and Profit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680-1830 (London:Pickering and Chatto, 2014)。
[49]有关美国国内大资产阶级沆瀣一气的文学著作也认同这一观点,参见:Jaher, The Urban Establishment; Seven Beckert, The Monied Metropolis:New York City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American Bourgeoisie, 1850-1896(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Betty Farrell, Elite Families:Class and Power in Nineteenth-Century Bost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50]马萨诸塞州的第二大产业——鞋靴制造业是由数以百计资本匮乏的企业构成的,就如同这一时期其他类别的制造业一样,它们是靠着小企业主的私人借贷来获得融资
的,参见:Alan Dawley, Class and Community: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Lyn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有关更广泛的大型金融机构与制造业投资之间的联
系不畅的信息,参见:Glenn Porter et al.,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Studies in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Nineteenth-Century Marketing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1)。大卫同
样观察到,如果抛开棉纺织工业和铁路运输业不谈,那么私募债券总体而言是不为人们所知晓的。政府债券往往无利可图,且有时甚至并不安全。参见:Davis, “Stock Ownership
in the Early New England Textile Industry,” 209。
[51]Thomas Dublin, Women at Work: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 and Community in Lowell, Massachusetts, 1826-18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 137; Laurence F.
Gross, The Course of Industrial Decline: The Boott Cotton Mills of Lowell, Massachusetts, 1835-1955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63.
[52]Ayer, Uses and Abuses in the Massachusetts of Our Manufacturing.
[53]从1836年到1860年,在位于洛厄尔的汉密尔顿公司中,本地出生的女工数量从737名锐减到了324名,参见:Dublin, Women at Work, 138; Vera Shlakman, Economic History
of a Factory Town, 138-150。
[54]在汉密尔顿公司中,居住在寄宿公寓中的工人比重从1836年时的四分之三减少到了1860年时的三分之一,参见:Ware, 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 4; Dublin,Women at Work, 138-139, 140-141; Gross, The Course of Industrial Decline, 24。在布特公司中,工人群体的文盲比例有所上升,从1838年时的11%上升到了1876年时的25%,参见:
ibid., 63。
[55]亨利·威尔逊,反对奴隶制度,脱离辉格党后筹建共和党,南北战争后积极帮助为黑人建立完整的政治、民权措施。曾任联邦参议员,1872年在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
政府任副总统。——译者注
[56]美国废奴主义者,曾为逃跑奴隶提供帮助。——译者注
[57]Sven Beckert and Katherine Stevens, Harvard and Slavery: Seeking a Forgotten History (Cambridge, MA: Privately printed, 2001); Craig Steven Wilder, Ebony Ivy: Race, Slavery,and the Troubled History of America’s Universities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13); Samuel Eliot Morison, Three Centuries of Harvard, 1636-193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287.
[58]William F. Hartford, Money, Morals, and Politics: Massachusetts in the Age of the Boston Associates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1).
[59]“The Danger That Threaten the Rights of Man in America” (July 2, 1854) an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Theodore Parker, ed. Frances Power Cobbe (London:Trubner, 1863), vol.1, 257,vol.6, 141. 有关经济民粹主义与废奴主义之间的交互关系,参见:Dean Grodzins, “ ‘Slave Law’ versus ‘Lynch Law’ in Boston: Benjamin Robbins Curtis, Theodore Parker, and the Fugitive
Slave Crisis, 1850-1855,”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Review 12 (January 1, 2010):1-33; Dean Grodzins, “Theodore Parker and the 28th Congregational Society:The Reform Church and the
Spirituality of Reformers in Boston, 1845-1859,”in The Transient and Permanent: The Transcendentalist Movement and Its Contexts, ed. Charles Capper, Conrad Edick Wright, and Austin
Bearse (Boston: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1999), 73-117。
[60]Grodzins, “ ‘Slave Law’ versus ‘Lynch Law’ in Boston.”
[61]Charles Sumner, The Works of Charles Sumner (Boston: Lee and Shepard,1870), vol.2, 81. 马萨诸塞州中的草根反对运动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但在19世纪早期,这些运动被
成功地控制住了,参见:Andrew R. L.Cayton, “The Fragmentation of ‘A Great Family’: The Panic of 1819 and the Rise of the Middling Interest in Boston, 1818-1822,”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2, no.2 (1982): 143-167; Harlow W. Sheidley, Sectional Nationalism:Massachusetts Conservative Leade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 18151836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8)。
[62]即自由土地党,一个曾经于1848—1852年美国大选中存在过的政党,反对将蓄奴制度引入美国的西部地区。——译者注
[63]Hartford, Money, Morals, and Politics; Steven Taylor, “Progressive Nativism: The Know-Nothing Party in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Journal of Massachusetts 28 (2000), 167-184;
John R. Mulkern, The Know-Nothing Party in Massachusetts: The Rise and Fall of a People’s Movement, New England Studies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0); Dale
Baum,“Know-Nothing and the Republican Majority in Massachusetts: The Political Realignment of the 1850s,”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4, no.4 (1978):959-986; William Gleason
Bean, “Party Transformation in Massachuset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ntecedents of Republicanism, 1848-1860” (Ph. D.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22).
29
30
过三代将成必然……但这样的手段极为少见,更鲜有成功”。[1]
发展的自然规律,“除非采取某些非常手段以抑制这一进程,否则富不
护自身地位的阶层,都终将无法免于衰败的结局,而这种命运正是事物
利弗博士明确地断言,任何像他们那种靠着商业利润而非贵族特权来维
葡萄酒,他们总是佩戴着洁白的假发并穿着饰有丝质流苏的长靴”。奥
在银制火锅中煮熟的鹿肉并畅饮从精心雕琢的器皿中取出的冰镇马德拉
成了腐化的绅士,“他们整日忙于驾驶自己的豪华马车四处游荡、享用
的行文基调掩盖住了作者内心焦虑的小说之中,这些年轻的贵族被恶搞
品质的无能之辈。在由奥利弗博士所著的那部脍炙人口的、以诙谐幽默
的观察体会时,形容这些年轻人是既缺乏阳刚之气又不具备高贵的勇敢
弗·温德尔·霍尔姆斯博士,在谈到他对年青一代毫无英雄气概这一特点
起过同时代观察家的信心。身兼执业医师和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的奥利
一代的肩上。然而,这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年青一代,却几乎从没有唤
而逐渐逝去或淡出,构建新型经济政治策略的重担便猛然落在了年青新
当新英格兰地区早年间工业化进程的总设计师,伴随着危机的加剧
万劫不复。
南方蓄奴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与卫道士,在道德领域他们更是百口莫辩、尊敬的个体的形象,也不可避免地一溃千里。更加糟糕的是,作为美国
投票给他们了。而最终,这些精英作为公众利益代言人以及社区中最受
赞美和传播,此时此刻亦显得空洞无比,新英格兰地区的选民再也不会
破碎,他们原先对于在自己治下所实现的“跨阶级和谐”与“英明治理”的
破坏性的。每一场竞选过后,这些大资产阶级所倚赖的政治载体便愈显
在看来其也不能例外,而对大量贫困的工薪家庭而言,这个进程是极具
作欧洲工业化进程的对立面,人们曾经认为这一进程温和而有益,但现
别提恢复到原先那种自我扩张的态势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曾一度被视
立起来的棉纺织工业体系,现已步履维艰,连产出利润都做不到,就更
一种四面楚歌般的悲惨境地。那个由他们煞费苦心地惨淡经营才最终建
击,19世纪50年代时波士顿曾风光无限的资产阶级,事实上已经陷入了
遭受着来自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的全方位打
困境之中的抉择
31
立联系——这一点同样重要,因为在阿摩司接下来数十年的职业生涯
英格兰地区出产的纺织产品打开销路;二来便是要与当地的精英阶层建
征程。他此行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来是要招徕当地的批发商贩,为新
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亲笔书写的推荐信件,踏上了前往美国南部的
方式。而在不久之后,劳伦斯便携带着由他的叔叔——一位在南方地区
过在城镇中几座棉纺厂内的学习实践,他了解并掌握了纺织工厂的运作
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商人,他的第一站就是棉纺织重镇洛厄尔,通
劳伦斯和美国南方的紧密联系早在其职业生涯的初期便已然建立。
劳伦斯在棉纺织工业中身居要津。[4]
斯筹措经营资金时的借贷来源。这些复杂的业务关系奠定了小阿摩司·
萨诸塞州医院人寿保险公司董事会中的董事,而这些机构又往往是劳伦
与此同时,他还是一家商业银行、一家保险公司以及前文中所提到的马
例,在由劳伦斯自己开办的公司当中,他既是财务总管又是公司总裁,而劳伦斯家族本身又是柯钦科公司的大股东之一。按照约定俗成的惯
斯公司”,并与“萨蒙福尔斯镇柯钦科公司”签订了排他性的代销协议,中经历过一段学徒生涯。[3]
1843年,他创办了作为专卖商的“梅森-劳伦
立事业而正式成为一名代销商之前,劳伦斯曾在由他叔父所承办的公司
让的继任者,也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一尝试的领军人物。在开启自身的独
儿子、阿伯特的侄子以及威廉·阿普尔顿的女婿,是棉纺织工业当仁不
业兴许就能触底反弹、东山再起。[2]
小阿摩司·劳伦斯,作为大阿摩司的
家当中的生产规模,并由此推动新一轮的关税保护,这样一来棉纺织工
他们希望通过与南方种植园主达成新的妥协来扩大棉花种植业在整个国
冲突爆发的保守人士而言,那种因循旧例式的应对之策显然更受青睐。
对于那些深深根植于棉纺织工业、近乎绝望地想要维持现状并避免
然不同的方向发展下去。
问,这两条背道而驰的路线将令波士顿乃至整个美国的资本主义向着截
营,挽救自身的名誉,并努力打造出一套全新的经济运行秩序。毫无疑
了坚守现状而进行的斗争当中;另一条则是主动加入废奴主义者的阵
条出路可供他们选择:一条是背水一战,将自己的全部身家都投入到为
他们也只能张开双臂拥抱挑战了。事实上,在这场危机之中大致只有两
自身前景的悲观预言以及他们所处的阶级那近在眼前的坍塌崩落之时,在忧郁地寻找着自身的出路。可尽管如此,当他们面对着那些有关他们
机爆发期间的大多数时段中,这些年轻人都显得意志消沉,他们基本都
倒”般的巨大潜力,尚不为人们所知。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危
在那个年代,潜藏在这群新一代的年轻人背后的那种“挽狂澜于即
32
与南方棉花种植园园主之间的联盟置于其他一切之上的使命感,让劳伦
制度为条件换取在堪萨斯州中实现废奴。[9]
一种将北方棉纺织工厂厂主
权威并安抚那些南部人士,劳伦斯提出以准许在新成立的州中施行蓄奴
者,在发生于堪萨斯州的冲突中逐渐占据上风时,为了维护联邦政府的
遣美国司法警察对废奴主义者采取强制行动。[8]
当支持奴隶制的殖民
得自由的黑人从法院中营救劫走后,劳伦斯在极度震惊之中更是要求派
叫沙德拉·敏金斯(Shadrach Minkins)的被抓获的逃亡奴隶,被一群获
升级时,以劳伦斯为代表的骑墙派被推入了窘境。而在1851年,一个名
街头与堪萨斯州中为了抵制《逃奴追缉法案》而爆发的暴动和抗议逐渐
使用和平的法律途径将奴隶制从堪萨斯州彻底根除。然而,当在波士顿
在幕后支持、资助了“新英格兰移民援助协会”的活动——该组织致力于
能游刃有余。对争议双方在1850年达成的妥协,他表示赞同,同时他还
始,凭借着这种中立而温和的身份定位,劳伦斯在行为处事的过程中尚
潜在风险,并将任何可能会导致严重对立的政策扼杀于襁褓之中。一开
不偏向身陷于奴隶制争端之中的任意一方,他寻求的仅仅是提前预知到
提。劳伦斯将自己定位为头脑精明、行事冷静的务实主义者,因此他并
认识到,棉纺织工业的繁荣与长久必须以廉价而可靠的原棉供应为前
植业和北方棉纺织工业之间的合作关系)的隐患都异常敏感。他清醒地
密无间的伙伴关系,导致他对任何可能威胁到区际合作(指南方棉花种
劳伦斯作为棉纺织制造商,以及他与南方种植园园主建立的那种亲
斯长久以来一直憧憬着的生意伙伴。
地区的来客,他们礼尚往来、充满善意,[7]
而这样的交往对象正是劳伦
管理者以及市镇中的商人,是与其意气相投的正人君子。对于新英格兰
着的伟大进程。劳伦斯很快便发现,当地的东道主——棉花种植园中的
壮丽的建筑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昭示着在这座不断崛起的城市中正在发生
表赞赏,同时他也注意到了城市中富丽堂皇的圣查尔斯酒店,这座宏伟
新奥尔良市中的那种倡导应以四海为家的法式浪漫主义情怀,劳伦斯深
相反,他最关心的是脚下这片广阔而欠缺开发的南部疆土。对于弥漫在
存在以及奴隶遭到肆意贩卖的客观事实并没有引起劳伦斯的过度注意,车,亦在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的州界上往来穿梭。[6]
奴隶制的现实
成捆的棉花被堆放得到处都是,而满载着身为黑奴的妇女与儿童的囚
印第安人袭击所留下的痕迹。他看到在不久前才刚刚被殖民的土地上,上,劳伦斯亲身体会到了发生在那一时期的土地投机热潮,观察到了由
穿行在1836年时的路易斯维尔、纳什维尔以及蒙哥马利的茫茫原野之
后的几次与之相似的远征,劳伦斯得以观察到快速拓展着的南部边疆。
中,他将与这些南方精英唇齿相依、同舟共济。[5]
借着这次旅行以及随
33
变过程中,这些年轻人清楚地感受到了原先曾经和睦的南北方关系逐渐
际,该群体中的年青一代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在这一令人震惊的心理转
制度产生冲击的新生思想心怀芥蒂,然而在19世纪50年代行将结束之
波士顿的上流社会一直对诸如废奴主义那类可能使人头脑发热并对现行
年青一代波士顿精英,则采取了一套截然不同的应对之策。长久以来,与劳伦斯的所作所为背道而驰的是,那些与棉纺织工业牵扯较少的
的联系并进行共同的努力。
事实上,直至南北战争的第一枪打响,该组织的成员之间还保持着密切
着与南方达成新一轮妥协方案的诉求,他们还曾向华盛顿发起进军。[16]
有违宪法的“个人自由法案”,都遭到了这一组织的残酷打压。最终,带
织,而无论是被他们视作大逆不道的“废奴主义会议”,还是被他们看成
伦斯还与一些前辉格党人一道组建起了“波士顿联邦储蓄委员会”这一组
甚至在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5]
当选了美国总统之后,劳
衷于追随“自由贸易”的风潮,而并不理会保护美国国内市场的提议。[14]
界范围内原棉需求的持续扩张而导致的价格提升,致使当地人民更加热
寥寥。北方民众将其视为陈腐过时的荒谬提案,而在美国南部,由于世
错愕的是,劳伦斯的种种努力不仅在北方毫无进展,就连在南方也应者
够让原先那种支撑了美国棉花经济的联盟模式重获新生。[13]
可令人感到
国规模最大且产生了最多收益的产业)相关的保护政策,他希望由此能
岸。劳伦斯对自己所在的党派施压,要求其尽力推进与棉纺织工业(美
义策略。按照这一策略,蓄奴区将一直延伸到密苏里线以南的太平洋沿
对开拓西部的忌讳,同时他也拥抱起了该党在对待奴隶制方面的绥靖主
凭借“冷静的头脑”对抗“狂热的冲动”为宗旨。劳伦斯收回了他早些年间
选人参加竞选,后者是一个极富代表性的美国政党,以坚守美国宪法、图重掌舆情。他曾先后于1858年和1859年作为美国党和立宪联邦党的候
在南北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劳伦斯曾花费了两年时间不屈不挠地力
来什么呢?”[12]
州的崩坏衰落以及这些州中优秀儿女的流离失所之外,这究竟还能够带
与白人实现平等,究竟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除了会导致美国南方各
劳伦斯坦白道:“我实在无法理解将600万黑奴解放,并让他们在政治上
运动上走极端,并将个人观点凌驾于宪法之上”。[11]
在自己的日记中,Andrew)这位马萨诸塞州的州长先生,劳伦斯则认为“此人喜欢在废奴
纳评价为“反对蓄奴制度的偏执狂”,而至于约翰·安德鲁(John
将约翰·布朗(John Brown)[10]
诋毁为“毫无爱国之心的大骗子”,将萨姆
斯最终走上了一条同情南部价值观并将废奴主义者视为死敌的道路。他
34
着中心地位,并经常从事与棉纺织公司相关的股票交易活动,但希金森
族一同长大。尽管由他父亲所经营的经纪人事务所在波士顿州街上占据
的新英格兰商人家庭中,而后在比肯山的居民区里,他与自己的远房亲
就斐然的投资银行家。1834年,希金森出生在一个传承悠久且人脉广泛
李-希金森,似乎生来便注定将成为南北战争后波士顿工商业秩序中成
的精英家族。在前文中所提到的发生在卡顿山的故事中的主人公亨利·
济秩序发展方向的杰出领袖,大多来自那些与棉纺织工业少有直接关联
那些在南北战争结束后开始显露头角的、决定了美国新型政治及经
邦军队。[22]
到了战争行为之中,并以一种令人瞠目的踊跃程度成群结队地加入了联
布,当局部性质的紧张与危机不断累积,他们终于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
以至于一同沉沦,亦不愿对南方地区的种植园园主俯首称臣而任人摆
述的一切心知肚明,他们既不想将自身的命运与棉纺织工业捆绑在一起
周知,而其生命也只能用风烛残年来形容。来自波士顿的年轻精英对上
续地遭受着来自政治方面的非议,棉纺织工业苟延残喘的颓势已是众所
织工业的态度绝非一成不变。身处一场漫长无边的经济衰退之中,又持
一线都与棉纺织工业息息相关,但事情的发展最终表明,学生对待棉纺
学生已然改换了阵营。[21]
尽管这些学生早年生活中的一丝一缕乃至一针
年,虽然此时哈佛大学的校方仍对废奴主义持反对意见,但作为主体的
化,而这一次,总算轮到由洛林来经受人们的唏嘘和非难了。[20]
到1860
一场公众冲突中时,在哈佛大学的校园内,人们的态度正变得愈加分
个名叫安东尼·伯恩斯(Anthony Burns)的逃亡奴隶的命运而卷入到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气氛骤然生变。1854年春天,当洛林因为一
支持。[19]
奴隶引渡原籍。至少在1852年时,学生对追缉逃奴这样的做法仍是鼎力
知名的保守人士,而后者正是美国巡回法庭中的执行专员,专司将逃亡
污蔑。他们将教授职位授予爱德华·洛林(Edward G. Loring)这样一位
想观念公之于众,便会对萨姆纳这位杰出而高产的法律学者进行攻讦与
在高校学术圈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权威人士而言,他们若想要将自己的思
言人,只能从学生那里获得无尽的唏嘘嘲讽乃至质疑怒斥。[18]
而对那些
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7]
在内的一批废奴主义代
该校的校园中,包括查尔斯·萨姆纳、贺瑞斯·曼(Horace Mann)以及拉
得最为突出。早些年间,该校堪称孕育保守主义思想的温床,那时,在
进思想。这种转变在哈佛大学这一备受棉花大王喜爱的民间机构中表现
走向崩塌,而他们自身也愈发倾向于接受那些可能会带来激烈冲突的激
35
伴。亚当斯家族作为声名显赫且与废奴主义运动羁绊颇深的政治世家的
出商业领袖”的小查尔斯·亚当斯,则是希金森的校友兼一同长大的伙
与此同时,另一位最终崛起为“主导了波士顿新型工商业秩序的杰
亲身经历了战斗,并因此而多次负伤。
被调配到了马萨诸塞州第一骑兵团中服役。在布尔朗和奥尔迪两地,他
代的洪流。希金森先是在马萨诸塞州第二步兵团中服役了4年,而后又
希金森26岁那年,他与许多哈佛大学前校友一起,满怀激情地投入了时
足其中。最终,直到南北战争正式爆发,他才被激励着采取了行动。在
政治,即便当原先那种局部化的政治冲突逐渐扩大升级时,他也未曾涉
活,且他的花费绝对超出了这些遗产所能够产出的利息。他基本上远离
暂的当下,希金森主要依靠自己从叔叔及祖父那里继承得来的遗产过
此刻,似乎任何受人尊敬的职业都无法进入希金森的法眼。[26]
在这一短
活,选择一份正经的事业,并将自己的热情和毅力投入其中。但是此时
己的父亲一直保持着联络,父亲曾多次恳求他放弃声色犬马般的闲适生
剧院交际,频繁招待那些从自己的家乡波士顿远道而来的访客。他与自
留驻足在奥地利的首府维也纳。他曾试图学习音乐,却总沉迷于在各大
春花费在了环游欧洲的旅行上,而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光景中,他都停
式已然行将就木。在随之而来的整个19世纪50年代,希金森将自己的青
随着蒸汽动力的粉墨登场,风帆时代正在悄然谢幕,这一古老的商业模
能,但总的来说,希金森并不过分热衷于这一古老的商业模式,毕竟伴
日后的职业生涯大有裨益的会计技巧,并初步磨炼出了自己的商业本
答、马尼拉、爪哇乃至澳大利亚等地。[25]
其间,希金森逐渐掌握了对其
期两年的学徒生涯。此时,这一商团的贸易网络最远延伸到了加尔各
(Samuel)和爱德华·奥斯汀(Edward Austin)的手下,开始了一段为
在希金森因病从哈佛大学辍学之后,他在印度码头商团中作为萨缪尔
内心最深处的动机,同样,他也并不清楚自己的奋斗目标究竟为何。[24]
者的说法,年轻的希金森对自己的人生尚不明确,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
在那个商业前景还不甚明朗的时代,按照曾为希金森撰写传记的作
说,希金森家族并不认为自己的延续需要倚仗于奴隶制度的存在。[23]
南方地区结交了许多朋友。”多年之后,希金森曾如此解释道。总的来
结识的人,无论他们是老是少,都对棉纺织工业有着极大的兴趣,并在
地接受废奴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在波士顿,许多能够为我们所观察并
成员,也正是因为如此,相比于他们的亲朋好友,该家族能够更加容易
要身份的同时,他们并非任何棉花产业相关公司的财务主管或是董事会
家族在一定程度上远离棉纺织工业的核心。在保持着自己作为商人的主
36
美国国内的南北对立以外,更会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组织方式产生
击。”[30]
小亚当斯极富先见之明地察觉到,原棉价格的飞涨除了会导致
理想场所,而这无疑将对美国南方垄断原棉供应的现状给予致命一
完工的、长达数百公里的铁路干线,已将广大的领域变成了棉花种植的
屿,都有可能会成为他们的聚焦之地。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印度那已经
法逾越的广袤荒野、遍布南美的高山台地还是点缀在太平洋上的零星岛
找出替代性的原棉产地。无论是印度次大陆的茂密丛林、非洲那看似无
方农业产区长久地执棉纺织工业之牛耳,因此他们必将放眼全球,并寻
地区在原棉种植领域的统治性地位。这些商业引领者绝不会坐视美国南
和身处曼彻斯特的实业家,将很快采取决定性的举措,以颠覆美国南方
治地位已是摇摇欲坠。小亚当斯如此推论道:“那些来自利物浦的商人
当斯所撰写的报刊文章中,他敏锐地做出了如下判断,“棉花王国”的统
他都在《大西洋月刊》的字里行间权衡着天下大事的轻重缓急,在由亚
亚当斯主要通过在报刊上撰写文稿来让自身与世界时事接轨。每一天,事务,与小亚当斯那巨大的野心相比极不相称。[29]
在那个时间点上,小
回奔波,并时常与对方发生争执。可以见得,这种碌碌无为的日常琐碎
开始涉足亚当斯家族的财富管理事务,他为了从租户那里收取租金而来
著名律师事务所中实习工作,并顺利取得了执业资格。与此同时,他也
后,小亚当斯曾将自己训练成一名律师,他在位于波士顿市中心的一家
希金森一样,小亚当斯对自己也没有一套明确的职业规划。在毕业之
轻时便有如幽灵一般萦绕在他心头,且久久不能消逝。更糟糕的是,与
尽管继承了显赫的血统,但那种对于家族衰败的忧虑在小亚当斯年
着新的财富来源,以期据此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
了多达数千美元的额外补贴。可是即便如此,小亚当斯仍然急切地寻找
议员和外交官的传统)的日常开销,还每年为该家族的新一代成员提供
资组合不但充分地支撑了老一辈亚当斯家族(他们承袭了家族作为国会
股票,在这些财产中所占到的比例微不足道。[28]
这种以保守性见长的投
中心或是昆西地区(他们的家乡)的房产,而那些与棉纺织工业相关的
系,[27]
但亚当斯家族从这份婚姻中得到的财产主要是一些位于波士顿市
所积累的财富必然与奴隶贸易、由奴隶所生产出的商品货物脱不开干
足海洋运输保险领域的先驱。尽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由布鲁克斯家族
Brooks)先生的第四个也是最小的一个女儿,后者既是商人也是最早涉
婚姻而袭得。布鲁克斯小姐是彼得·查尔顿·布鲁克斯(Peter Chardon Adams Sr.)与阿比盖尔·布朗·布鲁克斯(Abigail Brown Brooks)小姐的
着距离。该家族的财富,主要是通过老查尔斯·亚当斯(Charles F. 后裔,一向洁身自好,他们平素里和那些与棉纺织工业有关的投资保持
37
这是因为一来他并非为该产业而生,二来他也没能赶上该产业最好的年
质上说,库利奇与棉花产业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牢固,的过程中,绒布帮曾凭借暴力手段干扰并冲击废奴主义集会。然而从本
顿精英所组成的激进组织“绒布帮”中的一员,在美国逐渐走向南北战争
支持者一道,被归入反废奴主义者的阵营。库利奇在当时被看作由波士
收入。一时间,在政治立场方面,库利奇只得与其他那些棉纺织工业的
在“布特棉纺厂”担任财务主管的职位,而这份工作给他带来了稳定的月
的是,当托马斯几近破产之时,他的岳父威廉·阿普尔顿为他提供了
大人物之间建立起的扎实关系,帮助他们获取了急需的商业信贷。幸运
样,他与他的合作伙伴之所以能够免遭灭亡,完全是因为他们与富有的
到来的经济恐慌中,库利奇险些失去自己的一切,正如他自己记述的那
商人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便开始做起了自营贸易。在随后于1857年
并时常感到自己已被波士顿的主流社会排除在外。在作为学徒跟随一名
年返回波士顿进入哈佛大学就读时,他只能说出一口十分蹩脚的英语,人。当托马斯·库利奇最终结束了自己为期10年的欧洲之旅,并于1847
四个儿子,则被他先后送往位于日内瓦和德累斯顿的寄宿学校中长大成
中国广州,并当上了罗素商行的合伙人,而包括托马斯·库利奇在内的
(Thomas Jefferson)的曾外孙。在19世纪30年代,库利奇的父亲曾移居
从其母亲的角度来看,他甚至还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
比肯山的住宅区中出生长大,他是一个古老的新英格兰家族的后裔,而
会主义骑墙派。与自身所处阶级的大多数成员一样,库利奇也是在位于
亚当斯”等人相比,托马斯·杰弗逊·库利奇其人则更像是脚踩两只船的机
与“以保守主义为特点的劳伦斯”和“以前瞻性而见长的希金森与小
英阶层挽回了不少颜面。[31]
参与到革命性历史事件中的机会,他们也由此在公众领域为波士顿的精
与同志情谊的军旅生涯。这场战争赋予了小亚当斯和他的伙伴一个亲身
出来。他脚穿皮靴,花费数月的时间置身于旷野之中,过起了充满豪情
离了毕业后沉闷的职业生涯,还让他得以从原先社会环境的桎梏中解脱
极践行的参与者,而非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这场战争不仅让小亚当斯逃
也随即抱着极大的热情加入到了军事行动当中。在这场战争中,他是积
在小亚当斯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南北战争便轰然打响,而小亚当斯
终结后得以幸存的乐观主义分子”中的一员。
的动态本质,他将自己视为波士顿那些“坚信工业资本主义将在奴隶制
切变化的人士相比,亚当斯无疑更能适应那种深藏在政治经济表象背后
深远的影响。与劳伦斯那样的因深陷棉花经济体系无法自拔,而反对一
38
在1851年被重贬为奴之事而对宪法欢欣鼓舞的、波士顿最为富有且受尊敬的人士,如何广泛地支持逃奴追缉法案的信息,参见:Manisha Sinha,The Slave’s Cause: A History of
Kimball, On the Battlefield of Merit:Harvard Law School, the 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223-235. 有关那些为来自佐治亚州的逃亡奴隶托马斯·锡姆斯
[19]Charles Warren, History of the Harvard Law School and of Early Legal Conditions in America (New York: Lewis Publishing Company, 1908), 2:98;Daniel R. Coquillette and Bruce A. [18]Morison, Three Centuries of Harvard, 1636-1936, 290.
《论自然》。——译者注
[17]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美国思想家、文学家,诗人。爱默生是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美国前总统林肯称他为“美国的孔子”“美国文明之父”。1836年出版处女作
[16]Crouch, “In Search of Union,” 228, 232.
[15]亚伯拉罕·林肯,美国政治家、思想家、演说家,共和党人,美国第16任总统,黑人奴隶制的废除者。——译者注
[14]Johnson, River of Dark Dreams.
[13]Ibid., 200-201.
[12]Ibid., 218.
[11]Ibid., 226, 237, 217.
害。——译者注
[10]约翰·布朗,1859年曾领导美国人民在哈珀斯费里举行武装起义,要求废除奴隶制,并逮捕了一些种植园主,解放了许多奴隶。起义最终遭到镇压,约翰本人则被逮捕杀
[9]Ibid., 169.
[8]Crouch, “in Search of Union,” 104.
[7]Amos A. Lawrence to Amos Lawrence, Amos Lawrence Papers, vol.2, November 12 and December 22, 1836, MHS; O’Connor, Lords of the Loom,47-48.
[6]January 3, 1837 and January 10, 1837, Box 1, vol.2A, Diaries of Amos A.Lawrence, MHS.
[5]Crouch, “In Search of Union,” 53-57.
[4]Ibid., 76-78; Whit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 Hospit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awrence, Life of Amos A. Lawrence, 49-52.
[3]Barry A. Crouch, “In Search of Union: Amos A. Lawrence and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1970), 64.
University Press, 1995), 207-208, 442-445.
[2]Michael F. Holt, The Political Crisis of the 1850s (New York: Wiley, 1978),201; John Ashworth, Slavery, Capitalism, and Politics in the Antebellum Republic (Cambridge: Cambridge
[1]Oliver Wendell Holmes, The Autocrat of the Breakfast-Table (Boston, MA:Phillips, Sampson and Company, 1859), 304; Hall,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198-206.
中扮演关键角色。
的支持,他们有信心更有能力在未来数十年间的美国政治经济转型过程
虐的手段来驱策劳工。由于能够获得来自美国东部地区的巨量金融资源
致;他们求助于最新取得的科学技术突破,同时也时常采取激进甚至暴
们不断地挖掘着自身的商业本能,将自己的组织与管理技巧发挥到了极
配性阶级的衰败的鞭策,他们的行动往往体现出一种高度的紧迫感。他
整合到一起。由于受到了棉花经济体系崩溃的驱驰,以及其自身作为支
体系中的地位。他们长途跋涉、历尽艰险,努力地将财富积累的新载体
败),这些波士顿市民聚集在一起,深刻地反思了自己在整个国家经济
盾。[34]
但最终,为了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尽管如此也无法免于失
原本身为纺织工业制造商的波士顿精英,一直以来都对这一运动充满矛
提高工人对工资待遇的索求,并稀释掉新英格兰地区的政治权力,那些
必然产物。由于“西部大开发”这一进程,必将导致劳动力从本地流出,在这群波士顿专业投资人士的面前,它们也绝非由原有发展模式带来的
的美国西部地区的那些新兴的且有利可图的投资标的,并没有主动闪现
波士顿积攒的巨额储蓄产出了稳定且高额的回报。[33]
事实上,位于广袤
断萎缩、衰落的颓势,他们开拓出了革命性的新路径,并依循此道利用
颖而出的年青一代,在南北战争结束后出人意料地逆转了波士顿财富不
包括希金森、亚当斯以及库利奇在内的诸多从波士顿原有精英阶层中脱
身,并将自己重新定位为南北战争结束后波士顿金融领袖中的一员。[32]
景。这种实用主义性质的关系,让库利奇能够轻易从棉纺织工业中脱Abolition (New He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509。
[20]“The Slave Catcher’s Commissioner Rebuked,” Commonwealth (May 5, 1854);Coquillette and Kimball, On the Battlefield of Meri, 236-241, 265-266.
[21]Louis Menand, The Metaphysical Club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01), 23-32.
[22]Hall,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23]Ibid., 9.
[24]Ibid., 90.
[25]Ibid., 81.
[26]Ibid., 134.
[27]波士顿商人开展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从17世纪便开始了,而在19世纪早期,这种介入仍在以非法的形式继续着,参见:Hugh Thomas, The Slave Trade: The 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1440-1870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7), 259-260, 534; James A. Rawley,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A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81), 341-351。
[28]Edward C. Kirkland, Charles Francis Adams Jr., 1835-1915: The Patrician at Ba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65. Will of C. F. Adams,Proved at Dedham in the
County of Norfolk, on January 5th, 1887, Adams Real Estate Trust, 1871-1887, Adams Office Papers, MHS.
[29]Kirkland, The Patrician at Bay.
[30]Charles F. Adams, “The Reign of King Cotton,” The Atlantic Monthly, April 1861. 有关棉花经济紧随南北战争的全球转型过程,参见:Sven Beckert,“Emancipation and Empire:
Reconstructing the Worldwide Web of Cotton Production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he American HistoricalReview 109, no.5 (December 2004): 1405-1438。
[31]Charles Francis Adams, Charles Francis Adams, 1835-1915: Autobiography(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16).
[32]Thomas Jefferson Coolidge, The Autobiography of T. Jefferson Coolidge, 18311920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23), 1, 10, 13, 18; Ayer, Uses and Abuses in the Management of
Our Manufacturing; Gross, The Course of Industrial Decline.
[33]这些新兴的商业冒险无疑从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针对几条西部铁路进行投资的先驱尝试中吸取了灵感,但对于一座深受棉纺织工业惠及的城市而言,这些尝试都是相形
见绌的。在19世纪50年代以及南北战争刚刚结束的那段时光,西部商业冒险的金融可行性仍然存疑,类似的例子包括希金森在资金匮乏且迅速走向破产的俄亥俄石油公司中的那段
受雇经历,参见:Higginson and Barry, Life and Letters of Henry Lee Higginson, 240-247.有关波士顿于南北战争爆发前在美国西部地区进行的投资的信息,参见:John Lauritz Larson,Bonds of Enterprise: John Murray Forbes and Western Development in America’s Railway 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Arthur M. Johnson and Barry E. Supple,Boston Capitalists and Western Railroads: A Study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Railroad Investment Proc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Thomas C.Cochran, Railroad
Leaders, 1845-189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34]相关案例,参见劳伦斯针对吞并得克萨斯这一事件所发表的评论——“更多的领土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国土已经从大西洋沿岸延伸到了太平洋沿岸,而仅仅
凭借着我们相对稀少的人口数量,统治如此广大的国土几乎成了不可完成的任务。我们的领土已经太大了,而当年罗马帝国就是因此而衰亡的,她攫取得越多,就越是无法守住自
己已有的财产。”Quoted in Crouch, “In Search of Union,” 62.
39
40
有利可图的。[4]
中。在那个时代,尚没有任何以往的经验能够表明,开采这样的矿藏是
在这些深入地下的矿脉里,铜矿石的品位低,且杂乱无章地分布在其
金属铜才有产出利润的可能,这些砾岩带中的铜含量却仅有2%~4%。
之中。依照传统的经验智慧,一座被开采的矿脉至少要富含40%以上的
继显示出了即将耗竭的迹象,[3]
而新发现的铜矿则隐匿在低含量的基岩
19世纪50年代末,在整个半岛上规模最大也是产出最多的三处采矿点相
渺茫的“飞来横财”让人浮想联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投机活动。到了
石品位极高的矿藏才会有利可图。但这种出人意料的、发生的概率相当
560万美元的股息。[2]
由于铜矿开采和运输的成本极高,只有开采那些矿
资者总共向当地的采矿企业投入了1310万美元的资本,却仅仅收回了
上的94家采矿企业中,只有6家能够做到盈利。从1845年到1865年,投
铜,可就算这样,当地的铜矿开采产业距离完美仍然相去甚远,在半岛
上述的这种方法令半岛上的居民每年都可以产出大约6.35万吨的
形成的泥沙中分离出他们想要的金属。[1]
中分离出来,矿工会先用水力粉碎装置将矿石砸碎,再从矿石被砸碎后
会被装入铁桶中,而后依靠人力或是畜力拉升到地表。为了将铜从矿石
一点地开采出来。铜矿石被装进独轮手推车中推入矿道,在那里,它们
矿法的移民,不畏艰险地利用钻头、铁锹乃至炸药将铜矿石从地里一点
寻找着那些能够产出大量铜矿石的矿脉,来自科尼什地区的精通英式采
结,而一种成产业化规模的经营模式则取而代之。各种股份公司拼命地
被轻易开采出来的铜矿采集一空。这种原始的投机热潮很快便走向了终
勘探者的足迹亦很快便遍布森林湖沼,他们沿着地表和山脊将一切能够
了这片土地。此后,政府将这片土地开放给数以百计的勘探者,而这些
府便随即采取行动,从当地的齐佩瓦族(Chippewa)印第安人手中夺取
已经持续了接近20年的时间。在1842年于该地区发现铜矿之后,联邦政
生。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时,沿着苏必利尔湖而展开的铜矿开采活动,那里,他和同伴使铜矿挖掘作为一项资本高度密集的工业产业而得到重
里之遥的、位于密歇根州的基威诺半岛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商业成就。在
在经历了战争和连续两个棉花种植季后,希金森终于在距比肯山千
一炮而红的卡柳梅特-赫克拉铜矿
41
理者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矿山本身。阿加西斯坚持认为矿井应被重新设
由于利用地面设备处理矿石的能力获得了极大提高,这些新来的管
吨的矿石。[7]
分钟可以敲打矿石90次,依照这种方式,它们每天都可以处理重达800
昼夜地敲砸着矿石,砰砰砰的巨响永不停息”。两台笨重的冲压锤,每
的9月份,阿加西斯才正式宣布捣碎机实现了不间断的工作,“它们不分
捣碎站能够粉碎出规格一致的矿块,以供给自动洗矿机使用。直到当年
加西斯与他的员工不得不花费了数月时间试验摸索,才最终让水力冲压
运输作业。[6]
由于矿山中出产的矿石往往在密度和硬度上迥然相异,阿
还是冶炼工厂,都将能够利用从苏必利尔湖中开入的大吨位蒸汽船进行
米的运河,依靠着这条运河,无论是波蒂奇湖畔的矿山码头、储物仓库
力冲压捣碎站被连接在了一起。另一家附属公司则疏浚了一条长约2千
进行的,花费了数百万美元)。通过这条铁路,矿山与坐落在湖边的水
中穿行而过的铁道线路(这一工作是在阿加西斯的领导下由希金森掌管
相应需求,于是他指挥着工人修建了一条长达约8千米、从茂密的树林
头疼的问题,阿加西斯认为铜矿附近的溪流所能提供的水力,无法满足
的诸多瓶颈发起了攻坚作战。其中,冲压捣碎站的水力供给是一个令人
过。在来自波士顿的规模空前的资金的支持下,阿加西斯对开采流程中
单位金属铜的开采、提取成本,但此时,此等壮举还从未被人们实现
取铜,并使之有利可图的唯一方法。尽管这种做法可以在理论上降低每
“以一种超大的规模连续不断地经营运行”,是从低品位的矿石中提
功地让这一产业迈上了崭新的阶梯。[5]
业的运行。他在荒凉的旷野中度过了20个艰难的月份,在此期间,他成
木工程学学位,亚历山大于1867年3月被派遣到密歇根州,负责这项产
Higginson)的哥哥,同时还是一个名声在外的博物学家。由于曾取得土
项目的现场负责人,他是路易斯·阿加西斯的儿子,艾达·希金森(Ida 躬亲,以期亲自重塑整个产业的运营模式。亚历山大·阿加西斯是整个
Shaw)和亚历山大·阿加西斯不仅掌控着这次商业冒险的全局,还事必
络”整合为这一新兴事业的坚实后盾。他的两个姻亲昆西·肖(Quincy A. 金森公司所掌握的资源”和“由波士顿的富有居民所编织成的社会网
佐治亚州的一团乱麻中解脱出来之后不久,希金森便成功地将“由李-希
低品位铜矿,这是一处位于波蒂奇湖区的未经开发的矿体。在将自己从
季开始涉足铜矿开采这一产业,并为此而购置下了一座名叫卡柳梅特的
投资标的的重任,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去破解这一困局。他们从1866年夏
来自波士顿的投资者,肩负着为巨额资金寻找能够产出足够利润的
42
时的7257吨飞升到了1885年时的约23万吨,而这将近占到了同一时期美
国境内品位最低的铜矿石,这一新型运营模式带来的铜产量便从1871年
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仅仅凭借着从世界上最深的矿井中开采出在美国
总的来说,由这些波士顿人设想并最终付诸实践的新型经营模式取
加西斯将劳工的暴动归因为他们在处理员工不满问题时的过度软弱。[11]
工会组织的图谋不轨这件事情上,公司方面保持了持久的警惕心理,阿
涨,而在其他的时间则一律休想。”在对待“劳工骑士团”的蠢蠢欲动和
绝不能被任何人牵着鼻子走,工资只有在我们认为合适的时候才会上
势。[10]
阿加西斯指示监工在工资的问题上面对劳工一步不退让:“我们
前往镇压,军队随即将罢工的带头人拘禁,并帮助矿山的所有者重掌局
战告捷时,管理者紧急从底特律调集了所属美国第一步兵团的4个连队
他简易武器的劳工对峙,而后当警长与他的人马惨遭失败而劳工群体初
的。先是当地的警长带着18名警官与600余名装备着棍棒、石头以及其
1872年,这次罢工主要是由工资的减少和对更短的工作时间的要求引起
许工人联合在一起而采取一致行动。[9]
第一次主要的罢工活动发生在
另一方面,他们既不允许工人挑战自己在社区管理方面的权威,也不允
院和一所学校,并为由不同宗派的信徒所建立的诸多教堂提供支持。而
制度。一方面,他们设立了一家员工补助基金,在社区中建立了一家医
利裔等。在对待工人方面,希金森和他的伙伴采取了一种家长式的权责
区的主体则是那些外来的移民:康沃尔裔、爱尔兰裔、意大利裔、奥地
围绕着矿山而发展起来的社区已达到了约5000人的规模,而构成这一社
命工作着,同时,还有超过500名员工负责地面上的工作。到1875年,名公司员工一年到头都以一种异常规律的方式遵循着10小时轮班制而拼
在深入地下接近2千米,潮湿且充满硫黄气味的矿道中,多达1000
以及铜饼等成品。[8]
后这些粗铜会被运送到冶炼厂中提纯,并被最终制成铜锭、铜条、铜钉
后,在捣碎站中,人们会采用震动的方式把粗铜从沙砾中分离出来,最
重的蒸汽锤和一部波纹铁颚式碎石机把这些坚硬的矿石轧成碎渣。然
些矿桶运送到数百米之外的矿石加工厂中,在那里工人将使用一台6吨
下,这些满载的矿桶被拉升到地面上。最终,人们会利用高架轨道将这
擎的动力就算不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也是美国国内最强大的了)的驱动
重的矿石,而后在一台功率达到1000马力的引擎(在那个时代,这些引
在那里矿石会被倒入既大又重的矿桶内,而每一个矿桶都能够装载数吨
炸药和气钻来分离矿石,接着他们会将矿石运送到矿山的主要竖井中,计以满足更大规模挖掘作业的需求。在地下作业的矿工队开始使用高爆国铜总开采量的90%。[12]
随着这一事业的发展,被重新命名的“卡柳梅
特-赫克拉矿业公司”再也不是原先那家只靠单一矿井盈利的小型企业 ......
您现在查看是摘要介绍页, 详见PDF附件(4128KB,262页)。